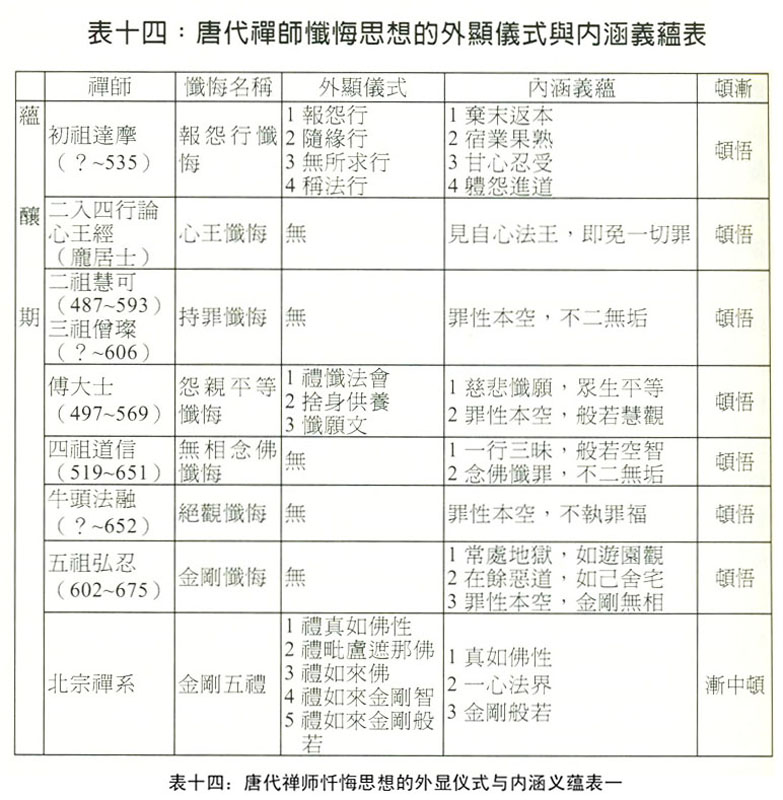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思维型态虽可假说为二类十二型,但十二型都是禅者以自身本具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进行忏罪的,他们的实践显现出四种特色:「非佛菩萨力量的自力忏罪」、「非礼忏仪轨化的自性忏悔」、「非罪相铺陈化的直觉自悟」、「非形上建构化的慧见自过患」,分述如下。
一、非佛菩萨力量的自力忏罪
这是从忏悔实践的主体而言的。大乘佛教的忏悔思想的实践,基本上都相信且至诚归依於诸佛菩萨的大誓大愿与大菩提心力,忏者藉由归依、礼拜与讽诵诸佛菩萨名号而灭罪清净,但这样的归依、礼拜与讽诵究竟是属于自力道还是他力道,1便成为忏悔实践的重要关键。
此处所谓的「非佛菩萨力量」,并不是在否定大乘佛教诸佛菩萨所发的大菩提心及无量无边悲愿,而是更强调忏者依於忏法而实践时,忏者本身即是一个忏罪的主导者,这主导者仍是无常、无我、性空的,但他以超越一切对立矛盾的本具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进行忏仪的践履,放下一切我执法执,在「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忏罪清净之後,身心便可继续精进不懈的自力精神。
佛陀的忏悔思想与历来禅者的忏罪精神都是这种自力精神的实践。从初期佛教经典看,佛陀不止一次教导弟子们要「恐怀後滞,就他致谢,即说忏摩之言」,真诚的「对人说悔」,「自责精进」。2从中国大乘佛教在汉、魏之间安世高、牟子博、昙柯迦罗、康僧会等人的忏悔实践来看,当时那种自力忏悔思想中的精进精神是不容置疑的。3晋代至梁代间,中国人迅速地将佛教拜讽诵诸佛菩萨名号而灭罪清净的忏悔理论与中国人期望灭罪消灾的现世利益目的融合在一起,4这看出佛陀的自力精神已渐渐地趋向於他力信仰。至大唐盛世,佛名忏悔与净土信仰又大肆发展,自力忏罪与他力忏罪的实践型态益形模糊,故义净才会对就时人的误解提出纠正,劝导佛教徒以「自责精进」的精神进行忏悔。佛教高僧大德将放下一切的「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及精进不懈的自力忏罪结合为一,是完全符合初期佛教的实修精神的。
从南北朝至唐代间各大宗派盛行的忏法来看,一般皆认为众生垢重、能力微薄而倾至诚心力将自身之业障託付於诸佛菩萨名号的弘大誓愿上,如梁译《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即直接礼拜「千位佛菩萨名号」以忏悔灭罪。5十一卷《佛名经》乃以「一一〇九三」位佛菩萨为礼拜对象,其後中国人又渐渐增加为礼拜「一万三千三百」位佛菩萨名号。6隋译《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灭罪经》亦直接依於「五千五百佛名及神咒」以除障灭罪。7《高僧传》载释超辩(420~492)日诵《法华》一遍,并以余力礼拜「千佛」名号。8《续高僧传》亦载释德美(575~637)每岁行忏,日礼拜「一万五千佛」名号,精诚所及,多感徵祥。9到了唐代三十卷《佛名经》时,已礼拜了「十八亿同名实体法式佛,十八亿同名日月灯佛,……三十六德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净王佛」,10这些都是以三世十方无量无边诸佛菩萨为礼拜忏悔灭罪之对象。此中,尽管《梁皇忏》精选出代表性的三世诸佛菩萨,以弥勒佛、维卫佛、尸弃佛等二十余尊佛菩萨为代表,11《水忏》精选出以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十六尊佛菩萨为代表,12仍容易造成他力忏悔的模糊认识。但到了晚唐宗密的《圆觉忏》,又以《圆觉了义经》、《华严经》、《法华忏》、《佛名忏》等为主,几乎礼遍佛教经典中无量无边诸佛菩萨名号,如於一万五千佛等一切诸佛外,遍礼十方尽虚空界微尘刹土中徹三世长短劫内广大智愿主伴互融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一切诸佛、十方徧虚空界微尘刹土中尽过去际一切化身诸佛般涅槃者分身舍利及诸灵像净图宝塔……乃至於诸大龙王及八部众并及土地灵祗、圭峰山神王、紫阁山神、護法善神、護伽蓝神主、道场神主、方主、地主、火主、风主、水主、山主、空主、药诸神众等皆为礼忏对象,几乎囊括了印度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的各种神祇。13此外,近世尚通行著《万佛洪名宝忏》,即约「万佛」为名,进行礼忏灭罪,消灾祈福;14至於《大悲忏》、《药师忏》、《净土忏》、《地藏忏》等,无不虔诚归依於诸佛菩萨之大誓愿力。15凡此,皆可看出中国大乘佛教仰赖诸佛菩萨之仪愿以灭罪消灾的他力道倾向。
这种他力道倾向的忏悔灭罪,固有其大乘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与教理的实践意义,但亦凸显出四大缺失:其一,是忏悔灭罪容易变成依赖他力才能灭除,忏者本身原有的力量变得很微弱,此与初期佛教的自力精进精神不类;其二,是具有多神论的倾向,既像印度教,又像中国道教或民间的混合宗教,容易偏离佛教缘起性空、无常、无我之根本教理,从而变成迷信。其三,不论是古代的封建社会,还今日民主开放的社会中,依赖他力而进行的忏悔对於那些佛教义理尚未正确认识清楚的初学者而言,容易因执著於外在佛菩萨之誓愿力而产生误导作用或不合佛法的反效果。其四,大乘佛教所说的三世十方无量无边诸佛菩萨,其实就是忏者自身,故禅宗乃有「心佛众生一体」、「即心即佛」之说,故若盲信於外在他力,极容易偏离佛教忏悔的本意。南传《长部》中,佛陀即多次强调不要依靠祈祷、礼拜、咒术、圣句、诵经等仪式来灭罪消灾,因为那都是徒劳无功之事。16圣凯认为,中国佛教的忏法虽是自力与他力的结合,但他力的作用,应该说是忏悔的一种「增上缘」,真正力量来自忏悔者的知罪、发露、发愿、回向,最後由智慧的观空而达到罪业清净,17亦强调了自力忏悔的主导作用。
唐代禅宗大师们偶亦以三世十方诸佛菩萨摩诃萨为礼忏对象,但他们不是将忏者的心力摆在归依、礼拜及讽诵诸佛菩萨名号上头,不因广大誓愿力与大菩提心而迷信礼佛拜佛,尤其反对一切形象、仪式或灵祗神主,而是将自己的本愿心力与诸佛菩萨的忏愿心力浑合为一,并直接将忏意密切联接到自己证悟禅境的修持功夫上,即以坚定专注的心力契应初期佛教佛陀那种自力忏罪的精进精神。18
这种自力忏罪的身心清净思想,普通存在於禅宗各大禅师的身上,从达摩的二入四行开始,就强调自力忏悔的能量,根本未提及礼拜诸佛菩萨名号之事,忏者是直接在理行二入兼用的禅进中实践报怨行忏悔;慧可时已有心佛不二之精神,故与僧璨间的忏罪是忏者自己直接进入超越内外中间的任运忏悔的灭罪活动中;道信的一行三昧无相念佛忏悔虽有净土宗的痕跡,但忏者自己在念佛的当下,是心是忏,是忏是佛,自然地忏除一切罪业,让身心运行在活泼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状态中;弘忍的金刚忏悔更是忏者自己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精神进行实相无相之忏悔;惠能的无相忏悔,是教导忏者自己不执著於一般人常说的禅定戒律,活用自身本有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与般若空智直接在自己的过患上忏悔灭罪;後来南宗的禅机忏悔,随机乍现,如神龙出没,无跡可求,忏者是直接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在现实的日常参禅生活中解禅证禅悟禅,针对自己的妄念妄想进行超越与灭除。
企图以礼拜诸佛菩萨的他力忏悔说唐代禅宗忏悔思想,是不合其自力精神的。
二、非礼忏仪轨化的自性忏悔
这是针对忏悔的仪式而言的。宗教借助於一定的仪式轨则来推行各种宗教活动,可以更明确地传达宗教者伟大、崇高、宏博与庄严的修行境界,佛教亦然。不过,佛教忏悔更重视运用高明的智慧形式来忏罪,它同样会在重要宗教活动中进行适切的礼拜仪轨,但高僧大德们都会清楚的说明仪轨目的绝不是在外在形式上而是忏者自身的初发心、大菩提心与无量誓愿。禅宗基本上未反对佛教各种礼忏仪节的合法性,只是他们反对过度依赖礼忏仪轨而丧失了主体自身即可忏悔的灭罪能力,故禅宗自达摩的报怨行即不是仪轨化的忏罪思想之实践,至惠能开始即明白的说他的无相忏悔是一种自性忏悔、大乘真忏悔。
严格言之,戒律不能完全等於忏摩,忏摩不能完全等同於忏仪,忏仪不能完全等同於忏法,忏法不能完全等同於礼忏,礼忏不能完全等同於忏悔,忏悔不能完全等同於忏罪,忏罪不能完全等於忏愿,忏愿不能完全等同於忏净。分别说之,戒律是透过戒条的认识与实践而让僧团清净教法永住之本,忏摩是初期佛教佛教徒在说戒仪式前的发露,忏仪是综合各种忏悔法的仪节总称,忏法是包含忏仪、忏理、禅观等的一部书籍,礼忏是虔诚恭敬的礼拜忏悔,忏悔是印度「ksama」和中国反省过失的「悔」字二字的合译,忏罪是忏者对自己的错误罪业进行忏除之意,忏愿是忏悔时的弘大誓愿,忏净是透过忏悔除罪而身心清净。但中国大乘佛教在实践之时,几乎都含糊笼统的把它们等同看待。等同看待的结果,很多人就以为忏悔就是忏仪,忏仪就是忏法,认为没有佛像、没有诵经、没有忏仪、没有礼佛、没有事忏、没有理忏、没有观相,忏悔似乎就不成立。事实言之,这只是随顺於一般忏法的忏悔仪轨而妄立的错误观点,初期佛教的佛陀,早就确立了自知自觉的「见过*(上←下→)发露*(上←下→)忏罪*(上←下→)灭罪」之忏悔义蕴,那是戒律、无常、无我清净心法的实践,萧子良的《净行法》与宋齐梁间君臣高僧们的忏悔文之撰写,其实都具备佛陀这种忏悔思想的呈现,而达摩至唐代禅宗大师们只是随缘摄其心法而专志践行之而已。
南北朝在建立礼忏法门的过程中,大致都遵循著道安(312~385)「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的五悔仪节。19天台智顗(538~597)的《法华三昧忏仪》、《方等三昧忏法》、《请观音忏法》、《金光明忏法》四大忏法,20华严一行慧觉(531~620)等人编制的四十二卷《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21宗密十八卷《圆觉忏》,都严格规定了严净道场、净身、三业供养、修三宝、请三宝、赞叹三宝、礼佛、忏悔、劝请、随喜、发愿、回向、行道、诵经、坐禅……等忏悔仪轨,作为修行者忏罪清净的具体实践方法。《梁皇忏》、《水忏》等忏法,亦在五悔仪轨的基础上加入各种忏行方便、禅定止观与灭罪思想。由於这种忏仪的制作皆有佛教经律论上的根据,罪相明白清楚,观行亦合於教法,极明显的与印度经律那种侧重於反复讽诵的编写方式不同,22避免了旧经律那种重复翻疊说法的繁冗情形,故中国人实践起来便觉得踏实而受用。中原之外,敦煌地区亦盛行著《法身礼》、《十一光礼》、《七階礼》、《金刚五礼》、《上生礼》等忏法,这些忏法除了依循基本的五悔仪轨进行礼忏外,并记载了密咒、和声、普诵、说偈等仪轨,增加了甚多的声情力量,对中国佛教的传播与深入民间,具有一定的意义。23
礼佛教忏仪轨是佛教徒用来印证修行境界的必要方式之一,且透过忏悔仪轨以进行讽诵,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逊于持戒和坐禅二大教法。24综观《大正》18~21密教部所有的经典,十之八九皆是密咒与念诵仪轨,可见密教是极重视念诵仪轨的修行意义的。但忏法与中国厚葬礼仪合一後,其思想便逐渐变化,如《北史》载:「(国珍)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25隋、唐三百余年间,礼忏法大为盛行,但社会上举凡七七斋、十斋、百日斋、一年斋、三年斋、归葬……等礼仪佛事已臻於商业化、等级化、制式化。26非惟初期佛教那种灭罪清净、身心安顿、精进不懈的精神已不存在,27连儒家那种孝道精神亦已完全质变。28元代以後,尽管朝廷禁止厚葬丧仪,对普罗大众并无劝阻实效。29明初之际,朝廷允许寺院依法进行经忏佛事,30虽有严格约束,亦未收到效果。31明·云棲祩宏(1532~1612)尝云:「水陆,头尾相连;经忏,接繁不断。求经次,汲汲如选官;请经师,忙忙如报喜」,32经忏佛事等已氾滥成灾。太虚大师尝说,经忏佛事本是从自己诚实悲切之心念经、拜忏,但世人多以「一二角钱了事」,原来诚心修行之美德尽失。33印光法师亦说过,忏者自己应「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一切佛事。」34印顺亦说过,经忏法事的氾滥,佛教徒的不僧不俗,代表著佛法衰落的现象。35
从教义实践而言,隋、唐以来诸礼忏法门所规定的仪轨并非不好,且可以由诸多忏仪的实践看出高僧大德们努力学佛修道的精进精神。36即使在元初之时,诵经礼忏以积极精进的思想仍然存在。37但是,当它与世俗灵魂不灭、因果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超渡亡魂、功德福报、厚葬亡者、消灾植福、金钱利益等观念同存并行、误解误用之後,佛陀教导世人体认生死无常、灭罪清净的忏悔思想便已失真。事实上,初期佛教时佛陀本身本来就反对「作吟詠声」、「诵诸经法」,即不赞成依照仪轨讽诵经典,38佛陀的本意是要求弟子们专心静默、净心学道、精进不懈,勿因俗尘杂事而干扰到无漏境地之修行。虽然後来允许弟子们「讚大师德」及「诵《三啓经》」,其目的仍是期许弟子们学习大师大德之修持功夫,并随时忏罪清净,认真去体认生命无常无我性空之理。39
相对於忏悔仪轨质变为经忏佛事,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实践便显得涵义充盈,力道十足,与顿悟见性禅法相辉相映。达摩的报怨行忏悔,即以「坚住不移」的定力与「舍妄归真」的方式直接针对如来藏自性兴净心中的「客塵妄想」进行忏除。到了六祖惠能,更在道信一行三昧无相念佛忏悔与弘忍金刚般若忏悔思想的基础上,衡量了唐代各大宗派的忏悔法,又摄约了大乘佛教《法华》、《华严》、《般若》、《楞伽》、《维摩》、《起信》等经论之无相禅观与忏悔菁华,提出「以三无功夫永断三世罪障」、「以七仪一心融般若禅行」、「以活泼心戒智慧禅定灭罪」、「一切法上念念不住的正念」四层意蕴的实相无相之自性忏悔,他不执於持戒、礼佛、诵经、禅坐、念佛、禅定与瑞相的观察,不执於多元样式的仪轨化忏悔。自性忏悔不一定要在寺庙中才能进行,不一定要制定严密的礼忏仪轨才能进行,不一定要有既定的人数、时间、日期之下才能进行,不一定要僵固在戒条、禅定与观慧的框架之中,不一定要事事忏之、禅观瑞相,不一定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系统才算忏悔,而是佛与众生原无差别、菩提即烦恼、菩提即烦恼,忏罪即行禅、行禅即忏罪之当下清净心的真如佛慧之自性忏悔。
虽然今本《壇经》亦载有简单的礼忏仪节,但那是无相戒壇上的基本仪节,无碍於自性忏悔的实践;神秀、神会、永嘉、百丈及北宗系统的禅师们亦偶见忏悔仪节的进行,但那都只是禅进成佛的辅助过程,至诚真心的自性忏悔并未稍懈;南禅五宗的禅师们,更活泼随机的在任何时空情境之中进行至心的忏悔,他们珍惜任何一个无常无我的当下,提起自己本有的自性清净心,面对眼前的宿世业力,无疑无惧,无思无虑,无住无相,接受之处理之忏除之,一切时中,勇猛精进。禅师们大多不会执著於一切形式意义的礼忏仪轨,如果有弟子一昧执著於形式意义的礼忏仪轨,必定会让禅师大为光火,像德山宣鑑(782~865)更彻底的否定形式意义的诸佛菩隧之礼拜仪节,只是「无事於心,无心於事」,以随机随缘的棒喝、眼神、动作、暗示等手法让弟子照见自性,忏悔清净。
企图以各大宗派的忏悔仪轨来说唐代禅宗的实相忏悔,亦不合其自性精神。
三、非罪相铺陈化的直觉自悟
这是针对忏悔发露而言的。忏悔的实践,忏悔主体必须有至诚真心的发露;依於忏法,忏者的发露即是忏理、方便、观行与总相别相的罪相之铺陈。唐代禅宗大师们没有否定各大宗派所制定的礼忏法,不会一味执著於形式意义的礼忏仪轨,但亦不会把忏悔视为罪相铺陈化的一一发露。所谓「非罪相铺陈化」,指的即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直觉自悟。
唐代各大宗派礼忏法门中之一一发露的罪相忏悔,就实践角度来说具有八重特殊效益:其一,从淬炼佛教经律论中的忏悔内容角度而言,具有青出於蓝而胜於蓝的殊胜意义与价值;其二,以特殊的罪相陈设作为自宗修行精进的礼忏要法,可以成为与他宗别具苗头的自家特色;其三,对於那些无法在经律论中汲取适切养分以利於一己修行的忏者而言,自家礼忏法中一一的罪相陈设具有导引忏者灭罪向善而易於入道的无上价值;其四,各大宗派礼忏法门的礼忏内容,有时是钜细弥遗的将三世罪业之总相、别相一一铺陈开来,这在现代社会看来,是颇具有科学性的知识价值的;其五,由於一一发露的大小罪相具有科学性的知识价值,故能为忏悔灭罪是否彻底作为有效的保证;其六,那些忏法在一一发露的大小罪相之前後,又加入忏罪因缘、三十七道品、本生故事、因果业报、六道轮回等教理,可让忏者同时认识佛法,而不是单纯的在忏悔灭罪而已;其七,可以透过礼忏法中一一大小罪相的细细发露与长时间之礼拜,达成收敛寺院僧众行为与提醒僧众再度认识佛教义理的作用;其八,在进行大小罪相的一一发露时,配合佛像的瞻仰、肢体的礼拜、梵呗的声音、团体的普诵与诗偈的唱诵等仪节,可以让忏者的忧烦情绪达到无形的医疗效果。
不过,各大宗派自经律论中所淬取的罪相忏悔内容,很多部分都是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时,高僧大德们为持戒修行而说出的,或为与外道邪说进行辨析论证而说的,或为行大乘菩萨戒等而说出的,这些六根造作而沦入六道轮回中的十大恶业罪相,它们当然与佛陀所说的忏悔思想可以相契,但刻意一一地陈设无量无边的罪相或戒律条规,容易成为僵硬呆滞的知识文字;基於缘起与罪性本空,本不需如《圆觉忏》般一一发露到近十九万字,更不需如《华严海印道场忏仪》一样礼忏到约二十六万字的内容;再者,忏悔乃由忏者自心的见过而发露,若再经过後人的编辑整理,便只是一套必须经过他人解释说明或记忆学习方能认知的范畴概念,这不但与佛陀亲身实践的自觉自悟之忏悔精进不同,更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直觉自悟自忏自净之自性忏悔不同。
禅宗不立文字,即不执著於知识概念;以心传心,即是以众生本有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去观罪性空,直觉宿世殃业的覆蔽,在直觉的当下自悟往昔的烦恼造作而忏除之,加上坚定禅观与理入二行,其精进不懈之精神与佛陀本心是千古辉映的。《宝林传》载僧璨在「觅罪不见」的当下,实已直觉罪性本空之理,後又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閒,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之语,即直觉过去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身心妄念之错误,故得慧可之心印。40这种直觉自悟的忏罪特色,完全是非知识概念的一一发露,而是《楞伽》那种超越心量的自觉圣智之精神,亦兼有《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无相空智,《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傅法正宗记》以下的禅宗传记都详加载录,所要呈现的即是禅者直心直觉自忏自悟的精进禅行。独孤及(725~777)〈镜智禅师碑铭〉说僧璨「以一相不在内、外,不在其中间,故足言不以文字」,41所说的亦是这种道理。
惠能在「佛性常清净」的基础下,又以高度的般若智慧言无相忏悔,更明显的呈现出直心直觉与自忏自悟的实修特色,如其云:「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於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直心是道场,真心是净土」、「但行直心,於一切法上无所执着」、「除妄不起心」、「众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自心除虚妄」、「当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自心归依觉」、「自心归依正」、「自心归依净」、「智者心行」、「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自性心地,以智惠观照」等说法,42皆是直心直觉的忏悟。崛多三藏甚至认为神秀的观心、看静(净)近於印度外道的禅法,那是一种「大误人」之事,只有以「直心」自看、自静(净)才是正确的禅法。43忏者以「直心」自看、自静(净),便能以正念行事,故惠能教导弟子们「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愚痴)(疽疾)染,从前恶行一时除,自性若除即是忏」,44念念自觉,念念自悟,自觉自性,自心自悟,即不被愚迷所染,不生烦恼业障,身心自然清净无碍,此即所谓「菩提本无树,明境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是也。45佛性既是本然清净,故连「无念亦不立」,忏者自己不必自寻烦恼的去「思量一切恶事」或「思量一切善事」,46因为善、恶亦是一种差别对立的知识概念,故「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思量毒害,化为畜生;思量慈悲,化为菩萨;思量智惠,化为上界;思量愚痴,化为下方。」47只要忏者於一切时中,念念自净其心,於一切境上不染,於自念上离境,不於法上念生,自然无造罪业。这种「念念自净其心」,「无念亦不立」的正念精进,即是忏者直觉自悟的忏悔。
南禅大师们的禅机忏悔,都是在惠能直觉自悟的无相忏悔之氛围下进行禅观生活的具体实践,他们很少在总相别相的一一罪相上另行发露。即使永嘉教导弟子们远离一切身、口、意,略见罪相铺陈,所用的方法仍是「行正直心」;48石头希迁更以「直将心来」、「有心无心尽忏除」落实在禅师与弟子对话间当下心心交会的禅印上;49马祖道一亦云:「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50,更教人以平常人的直会本具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不必执著在各种罪相的唱诵礼拜。永嘉的「三业清净」,强调的即是绝相离明与境智双寂;黄蘖的「一心精进」、马祖的「不作不食」、百丈的清规忏悔後的进一步「努力猛作」,所谓:「光阴可惜,刹那不测。今生空过,来世窒塞」的自我鞭策之灭罪精进。51是故,他们截断众流,无念亦不立,在日常生活之中忏罪清净,於一切时的行住坐卧中,皆以高度的直觉真心自忏自悟,与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因缘业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一体如如,禅悟不礙忏悔,忏悔不礙禅悟,禅悟因忏悔而得落实,忏悔因禅证而发挥效力。一一罪相的铺陈礼拜与讽诵,对直觉自悟的禅宗而言,便显得多余而累赘。
企图以各大宗派的罪相铺陈来说唐代禅宗忏悔思想,更不合其直觉精神。
四、非形上建构的慧见自过患
这是针对忏悔的思想实质而言的。唐代禅宗忏悔思想既不是依赖「诸佛菩萨的力量的自力忏罪」,亦不执著於「礼忏仪轨化的自性忏悔」,更不是「罪相铺陈化的自觉自悟」,则其思想实质明显是禅者主动的从知识概念的铺陈堆砌中蝉蜕出来,切入忏悔主体本身在行住坐卧的当下因无明所产生的各种烦恼过患诸罪业上,具体的掌握住忏者最迫切要解决的焦点,而不是再堕入於世俗的知识或哲理角度建构出新的形而上体系。
此处所谓「各种烦恼过患诸罪业」,指的现实人因无常、无我、缘起性空、无明而造作的罪业,在因缘条件的聚合下,逐渐累积成毒疮、洪水、猛兽,随时侵蚀啃噬本来清净的真如佛性,故它不是一般哲学从存有论立场所说的心灵主体之行为,亦不是从心理学而说的情绪与人格,尤非一般宗教所说的因果轮回与罪报。西哲如亚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曾建构过各种形式逻辑、道德哲学、自然科学等的形上体系,52他重视因果问题的论述,却仅止於形式逻辑的推理与证成,并不是去探讨一个现实人因无明造作的惑业苦报,当然亦非忏者自作自受的因果罪业之忏除。又如十八世纪的康德(Kant,1724~1804),提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大哲学论著,建立起独特的批判哲学体系,53他也承认因果规律,但未能把洞见予以充分说明与证成,并把人类可能本有的「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推给至高无上的上帝,使得很多真理都变成昏暗。54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虽否定了康德的上帝创造说,55从人的存在(此在,Dasein)基础上重建存在论,但一生都围绕在「语言与存在」主题的思辨上,56亦不是如佛教一样就无明造作的惑业苦报提出解决之法。
隋代智顗以「一心三观」、「四种三昧」与「三谛圆融」思想建构了天台宗的圆融无碍妙旨,透过「五时八教」的判教证成自家的圆教体系。57他特别制出《法华三昧忏仪》、《方等三昧忏法》、《请观音忏法》、《金光明忏法》四大忏法,并将四大忏法纳入「四种三昧」中,而「四种三昧又是「十境十乘观」的外缘,从事相升到理法,再佐以「一心三观」,最後契入中道实相。58他亦主张观实相的无生忏悔,但诸多仪轨之践行、诸多罪相之唱诵,虽成就了大教之礼仪,却有溺於形式意义之缺失:《法华玄义》、《维摩诘经玄疏》、《摩诃止观》59等著作的思维体系虽有庞大深邃而严密的逻辑形式可寻,但一般忏者若未就逻辑形式进行认识与辨析,中道实相亦难证成,且严密的逻辑形式本就是被佛陀默然否定的思想。
初唐杜顺(557~640)《法界观门》一书建构起华严「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徧含容观」三重观门哲学系统。60法藏(643~712)、澄观(738~839)或宗密(780~841)诸祖再推衍十玄门,由十玄门而六相圆融,论成多重义理的思维系统。61方东美认为,华严宗的法界三观为机体统一之哲学,可以解决一切哲学上主客空有对立难解诸问题。62但一行慧觉(531~620)等人依於《大方广佛华严经》所编撰的《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浩浩四十二卷近二十六万字的礼忏仪轨所呈现的「十重行愿常徧」之深奥哲理,非惟一般华严僧徒难以透过礼忏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世俗人等更是望而却步。63宗密依《圆觉了义经》所制作的十八卷《圆觉忏》,以「道场法事七门」、「礼忏法门八门」、「坐禅法八门」践证「毗卢遮那、文殊普贤、三圣性相身」的「圆通理智」。64但强调哲理的现象与天台忏法不相上下,且要求忏者要在「一百二十日」、「百日」或「八十日」的期限内完成;将近十九万字的浩繁内容,忏诵时易有疲倦昏愦之失;壇场设内外,悉有严净之要求,与佛陀的随处清净意并不相类;忏者的前後准备功夫极严谨,稍一疏漏即属非法;加上难以计数的诸佛菩萨名号与偈语之礼拜忏诵,道场均须昼夜六时,夜以继日,「不计身命,尽未来际,修行此法,三期限而不懈怠。」65此种冗长繁富的忏仪礼拜与忏罪精神,固可帮助忏者体证华严哲学之深奥玄义,亦因徒具形式意义而无助於世人忏罪清净之用。
唐代禅师多教导忏者以定慧不二或戒定慧一体的如如不动智慧观照行住坐卧的当下身口意的烦恼过患之现起,任何一个人都可在现起的当下忏悔除罪清净,继续时时进行的禅观精进,这本就是初期佛教佛陀忏悔精神的思想实质,亦是直接从印度佛教忏悔思想的了义处、胜义谛加以落实到忏悔灭罪的具体实践。从达摩二入四行的报怨行开始,忏悔就是众生自己针对「受苦时」的因果罪业之认识而「甘心忍受,都无怨雠」,「与理相应,体怨进道」,66这不是形上哲学之建构,而是众生的自知自觉的观照与实践。中间慧可僧璨罪性本空的认识,亦是在当下慧见妄想而忏罪清净,传递禅宗心印。道信的一行三昧无相念佛忏悔,所用的是缘起性空的般若空智,并不是高深玄奥的形上哲思系统。惠能以定慧不二禅的无相忏悔,一样有「无相偈」→「自蹄依三身佛」(无相戒)→「发四弘大愿」→「无相忏悔」→「无相三归依戒」(归依三宝)→「灭罪颂」→「无相颂」七个忏悔进程,但他的无相忏悔是忏者在如如不动的定慧不二禅观下照见自身的烦恼过患,虽然可以整理出「以三无功夫永断三世罪障」、「以七仪一心融般若禅行」、「以活泼心戒智慧禅定灭罪」、「一切法上念念不住的正念」四层思想义蕴,并不是在建构形上哲学,而是在教导忏者於逼切时中见过忏净。
神会在惠能无相忏悔的基础上开展出以《金刚经》为据的「般若知见」之无念忏悔,从敦煌写本的相关作品来看,其中至少具有「不执罪福的愿罪除灭」、「三无漏学的清净无念」、「实相无相的般若忏悔」、「无住立知的正见无念」四层思想义蕴。但这他是以《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之四无相境界去开展他那与三无漏学浑融为一的无念无住之忏悔,是一种教导现实之人依於正知正见进行自见自忏自证的忏悔。南禅禅师们顿悟见性的禅法中,每每於话头、叫喝、棒打、眼神、动作、暗示、反诘或偈语中呈现出忏悔思想,他们大多绝相离言,故纵有忏悔仪轨的实践,亦与达摩—惠能—神会的精神一样,在千姿百态的禅行实践中,如如不动智慧观照行住坐卧的当下身口意的烦恼过患之现起,在现起的当下忏悔除罪清净,继续时时存在的禅行精进。
企图以形而上哲学建构来说唐代禅宗忏悔思想,是无法契合禅宗大师们「见自过患」之忏罪精神的。
上列四种忏悔的实践特色,不论是由「自力忏罪」到「自性忏悔」,还是由众生的「直觉自悟」到现实人心的「慧见自过患」,都是肯定《涅槃》、《楞伽》、《起信》等所说的「众生皆有佛性」、「罪性本空」等义涵下去进行的,众生在自知自觉自己的自性可以有忏罪—灭罪—清净的能力下,一行直心,常见自身过患,不赖任何形式戒条、形式忏仪、形式禅定,自能自忏自净,故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四大实践特色可图示如下:
1 自力道与他力道各有不同的严密组织与实践方法,二者在教理史上都占有重大之地位与影响,他力道的实践是深信阿弥陀佛的如来本愿之至心念佛,自力道则以禅者自己的初发心为基础,将无限的永恒摄受於现在一刹那间,约摄万行於一行,将雄大的无限悲愿把握在眼前具体的一事中。参:佐藤泰顺〈自力道与他力道〉,载印海译《中国佛教思想论》,(U.S.A.,法印寺,1996年11月),页251~300。
2 《大正》23,No.1442,页706上。
3 详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之论述。
4 塩入良道〈中国佛教における佛名经の性格とその源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n.42,(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6年11月),页221~319。
5 《大正》14,No.447a,页376上~383中。
6 事实上,南北朝礼拜佛菩萨名号的经典甚多,除了敦煌的十一卷《佛名经》外,其他如梁·僧佑(445~518)《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律论录第一》中记有西晋·竺法護(239~316)译之《贤劫经》七卷、《诸方佛名经》一卷、《十方佛名经》一卷、《百佛名经》一卷、东晋·竺昙无蘭(381前後)译之《贤劫千佛名经》一卷、东晋·鸠摩罗什(344~413)译之《新贤劫经》七卷、《称扬诸佛功德经》三卷等;同书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所记载之《诸经佛名》二卷、《三千佛名经》一卷、《千佛因缘经》一卷、《过去五十三佛名经》一卷、《五十三佛名经》一卷、《贤劫千佛名经》一卷、《南方佛名经》一卷、《现在十方佛名经》一卷、《五千七百佛名经》一卷等皆是。又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众经别生四》,亦举出《佛名经》一卷、《贤劫千佛名经》一卷、《佛名经》十卷、《十方佛名经》二卷、《百七十佛名》一卷等近三十部。详拙著《慈悲水忏法研究》,页77~78。
7 隋·阇那崛多译《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灭罪经》,《大正》14,No.443,页318上~322下。
8 《大正》50,页408中。
9 《大正》50,页697上。
10 《大正》14,页292下~页293上。
11 《大正》45,No.1909,页922中~967下。
12 《大正》45,No.1910,页967下~978中。
13 《卍新续》74,No.1475,页375上~511下。
14 如河北省河间市千佛寺於2008年2月举办为期十天的《万佛洪名宝忏》法会。参网页:http://big5.fjnet.com/fwzt/t20080122_62290.htm,2008/3/5。台湾中台禅寺亦常进行《万佛洪名宝忏》法会,参网http://ctzen.org/sunnyvale/download/2007_1_3_Dharma_Events_Chines_V3-2.pdf。另见http://www.ctworld.org.tw/108/puyin4/index.htm,2008/3/5。又香港大埔定慧寺亦曾於2007年11月26日至12月举行《万佛洪名宝忏》法会,迴向世界和平,人民安乐,百业俱兴,参网页: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71/571_18.html,2008/3/5。
15 林子青〈忏法〉,收入吕澄等《中国佛教人物与制度》,页455~461。
16 相关资料甚多,可参南传《长部》1,《汉译南传大藏经》6,页78、260等处。
17 圣凯《中国佛教忏法研究》,页401。
18 《四分律卷三十五·说戒犍度上》,《大正》22,No.1428,页817下。
19 宋·净源《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第一·总叙缘起》,《卍新续》129,页1上~下。
20 详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第四章智者大师所制四部忏法」,(台北:法鼓,2000年9月),页83~244。
21 唐·一行慧觉录,宋·普瑞注,《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四十二卷,《卍新续》74,No.1470,页139上~360中。
22 除了一般经文的重复翻叠之外,在阿含经亦常见主角人物把所欲表达的意思重复诵说三次(三啓)或多次的情形,如《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三·(604)经》,《大正》2,页162中。又如《杂阿含经卷三十八·(1076)经》,《大正》2,No.02,页280中。
23 关于敦煌地区礼忏法的忏仪、声情与思想,详汪师《敦煌礼忏文研究》,(台北:法鼓文化,1998年9月)
24 蓝吉富〈讽诵在大乘佛教中的意义〉,收入释恒清编《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印顺导师九秩华诞寿文集》,(台北:东大,1995年4月),页445~454。
25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八十·列传六十八·外戚·胡国珍传》,页2688。铣按:「七七斋」的礼俗是由佛教与《七毗婆沙》及《瑜珈论》而来,所谓中阴身七日转生,七日不转生,最迟至七七日必然,是故佛门诵经咒,必以七日为度。参:王贵民《中国礼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初版一刷),页181。
26 徐吉军《中国丧葬史》,页340~415。《新唐书卷二十·志十·礼乐十》,页454~456。
27 参拙文〈「佛说无常经」的传译语丧葬礼仪〉,《中华佛学学报》第二十期,2007年7月,页65~104。
28 《十三经注疏8·论语注疏卷二·为政》,页16。
29 如元朝政府为纠正厚葬劣风,亦颁文规定:「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室,金银为马,杂綵衣服『帷帐者,悉禁之。」明·宋濂撰,《元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三·刑法四·禁令》,页2682。
30 清·仪润撰,《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五·住持章第五·念诵》:「凡念诵,或常住自办,或施主发心,俱当预定:今约施主例,尊官到,知客同住持迎接。若非尊官,客堂接待。预日设壇严净,掛牌。(牌云)本月(某)日(某)职(某)護法,为(某)事,诵(某某)经,顶礼(某)忏,共若干日。诸师挨次轮日,每日几名,开列於左。(某甲)首座师。(某甲)西堂师(云云)。」见:藏经书院版,《卍新选辑·禅宗部二》,(台北:新文丰,1984年3月再版),页663上。
31 《卍续选辑·禅宗部二》,页663下~664上。
32 《卍续选辑·禅宗部二》,页663下。
33 太虚《勤俭诚公》,《太虚大师全集》N.35,(北京:宗教文化,2005年),页95。
34 印光《灵严寺永作十方记》,《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页148。
35 见:印顺《华雨集(四)·中国佛教琐谈》,页129~页142。。
36 关于此方面之观点,参拙著:《慈悲水忏法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参、关于忏法一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1月,页29~42。
37 《卍续选辑·禅宗部二》,页663下。
38 据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第四·第一门第四子摄颂之余》:「佛云:苾芻不应作吟詠声,诵诸经法,及以读经请教白事,皆不应作。然有二事作吟詠声:一、谓讚大师德,二、谓诵《三啓经》,余皆不合。」《大正》24,No.1451,页223中。又见《长部》1,《汉译南传大藏经》6,页118、260
39 参:拙文〈「佛说无常经」的传译语丧葬礼仪〉,《中华佛学学报》第二十期,2007年7月,页65~104。
40 见《禅宗全书·史传部(一)》,页319~320、323~324、325。又见:柳田圣山《达摩の语录:二入四行论》,页220~221。
41 《全唐文新编卷三九〇·独孤及》,页4480。
42 以上分见《六祖壇经》,页35、43、51、55、65、67等处。
43 崛多三藏至大原定襄县曆村,见神秀弟子「独坐观心」,师问:「作什么?」神秀弟子对曰:「看静!」师曰:「何不自看!何不自静!……西天下外道所习之法,此土以为禅宗也,大误人!」《祖堂集卷三·崛多三藏》,页65。
44 《六祖壇经》,页53~54。
45 《六祖壇经》,页27。
46 《六祖壇经》,页45。
47 《六祖壇经》,页45~46。
48 元魏·菩提留支译《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大正》9,No.0272
49 石头云:「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直将心来。」大颠对曰:「无心可将来?」石头曰:「先来有心,何得言无心?有心、无心发同謾。」我(大颠)於此时言下大悟此境,却问:「既令某甲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和尚意须除之?」石头云:「我除竟!」《祖堂集卷五·大颠和尚》,页94。
50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诸方广语·江西大寂道一禅师》,《大正》51,No.2076,页440上。
51 《卍新续》63,No.1239,页230中。
52 D.J.Oconnor(奥康诺),洪汉鼎译,《批评的西方哲学史》(上),(台北:桂冠,2004年2月),页161。
53 《批评的西方哲学史》(中),页799~852。
54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4月5刷),页6、16。笔者按:牟氏所谓「智的直觉」,虽纵指儒释道三家所共有的人的先天本能智慧,但最终仍倾向於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这与佛家无常、无我、缘起性空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智慧观照依然不同。
55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71年3月),页43。
56 孙周兴〈在思想的林中路上〉,氏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页4~5。
57 隋·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一、卷十,《大正》33,页681下~692下、页800上~814上。隋·智顗《法华经文句》卷六下,《大正》34,页82上~90中。
58 圣凯〈天台忏法的形成及其思想〉,收入氏著《中国佛教忏法研究》,页79~113。
59 《妙法莲华经玄义》,《大正》33,No.1716,页681下~814上、《维摩诘经玄疏》,《大正》38,No.1777,页519上~562中。《摩诃止观》,《大正》46,No.1911,页1上~140下。
60 除了《法界三观》外,学界认为《华严五教止观》(《五教止观》)亦是杜顺之作品,然稍一留意,即知为後人伪托之作。参:持松(1894~1972)《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台北:华严莲社,2002年10月版),页26。
61 陈英善〈就华严法界观门论华严思想之演变〉,《中华佛学学报》第八期,1995年7月,页373~396。
62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1981年7月初版,1992年11月5版),页1~70。
63 唐·一行慧觉录,宋·普瑞注,《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四十一卷,《卍新续》74,No.1470,页139上~360中。
64 《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卷一·道场七门·一劝修》,《卍新续》74,No.1475,页376下。
65 《卍新续》74,No.1475,页376上。
66 此据《菩提达摩四行论》,《禅宗全书·语录部(一)》,页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