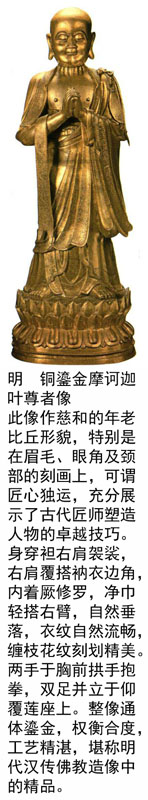结集是一个佛教名词,原意为会诵。就是众多佛教徒集合在一起,背诵出释迦牟尼的教言,共同审核确认。
释迦牟尼逝世当年,由大迦叶主持的这次结集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所以称为“第一结集”。
第一结集由大迦叶主持召集,参加者据说是五百个已经得到阿罗汉果位的比丘。所以后世又把它称作“五百结集”。学术界认为,从第一结集起,佛教开始有了初具雏形的经典。
当时结集的具体方法是先由一人将他平时听到的释迦牟尼的教诲复述出来。复述时必须先说明释迦牟尼的这一段教诲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当着哪些人讲的,然后由参加集会的其他弟子们共同审定真伪,看这个人讲的是否与自己平时听到的释迦牟尼的教导相符。大家共同认可的,就作为释迦牟尼的遗教正式确定下来。现存佛典一般都以“如是我闻”开头,表示这是复述者复述的。然后以“一时佛在某某处与某某人俱”,说明释迦牟尼说法的时间、地点、参与者等等,就是这种会诵形式的反映。佛典开头的这部分内容,后代称为“证信序”。佛教认为证信序有六种功能,称为“六事成就”,又称“六种成就”。即:
第一,“如是”两字是“信成就”。要相信阿难所宣说的,的确是佛本人所说。佛教传统认为:“佛法大海,唯信能人。”对佛经能够信而不疑,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我闻”两字是“闻成就”。就是确认这些经文的确是阿难亲自听到的。阿难是这部经典的复述者。
第三,“一时”两字是“时成就”。即交待说法的时间。
第四,“佛”字是“主成就”。即交待说法的人。佛是世间与出世间说法化导之主,故称主成就。
第五,“在某处”,是“处成就”。即交待说法的处所。
第六,“与某某人俱”,是“众成就”。即交待参与听法的人。
佛教传统认为,证信序是正规佛经必需具备的基本形式。凡是不具备这种形式的经典,其真实性往往会受到怀疑。
据《五分律》等典籍记载,第一结集时,“多闻第一”的大弟子阿难背诵了释迦牟尼对佛教教义的许多论述,这些论述被大家肯定下来之后,便称为“经”。号称“持律第一”的大弟子优波离则背诵了释迦牟尼关于僧人修持与教团生活的各种规范,这些规范被肯定下来以后,便称为“律”。从此,经与律由此成为佛教典籍的基本组成部分。
同佛教史上的其他问题一样,不同的佛教经典对第一结集到底由谁主持、有哪些人参加、由谁背诵遗教及会诵、厘定了哪些典籍,说法各不相同。如《四分律》等经典主张,第一结集时,阿难除了背诵经之外,还背诵了专门解释经中奥义的“论”。后代佛教把经、律、论当作佛教经典的最基本组成部分,称作“三藏”。也就是说,《四分律》主张早在第一结集时,三藏已经齐全。《付法藏因缘传》也主张三藏早就齐全,但认为论不是由阿难,而是由迦叶背诵出来的。但《迦叶结经》则说经律论三藏都是阿难背诵出来的。另外,有些经典还主张,除了迦叶在王舍城灵鹫山主持的结集之外,还有其他人在其他地方也举行了对释迦牟尼遗教的结集。如《大唐西域记》卷九称,在迦叶召集五百上座举行结集的同时,有数百千比丘举行了另一个结集。并会诵了经藏、律藏、论藏、杂集藏、禁咒藏等五藏。《大智度论》与《金刚仙论》则说,第一结集时,弥勒与文殊师利及十方佛在铁围山外,结集出大乘法藏。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的说法,这儿不一一列举。
学术界认为,第一结集时,佛弟子们把释迦牟尼的一些教导会诵出来,形成最初的佛经,这是可以信从的。现在佛经中保留了一些比较古老的偈颂,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之类,形态比较固定,在经典中出现频率较高,它们很可能就是第一结集的作品,甚至很可能就是释迦牟尼的原话。但是,当时是否已经形成完整的经律论三藏,尚可怀疑。至于说结集出杂集藏、禁咒藏等等,那完全是后代的附会,不足凭信。所谓结集出大乘法藏云云,也显然是大乘产生以后的传说。所以产生这些附会与传说,主要因为佛教后来分成许多派别,每个派别为了争取正统地位,为了维护自己学说的权威性,都把自己这一派经典的产生上溯到第一结集,由此编造出对自己有利的传说。在古代,这是毫不足怪的。
第一结集虽然编纂出最初的佛经,但未能摆脱口口相传的传统,没有把编成的佛经记录为文字。而且,各地教团都用自己所在地的俗语来传承佛典,没有统一的标准语。这样,在佛教向各地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理解的歧义与传承的讹误,甚至产生各种人为的篡改,这也是佛教后来分裂成许多部派的原因之一。据《付法藏因缘传》记载,阿难在一次行化中,来到一个竹林,听到一个比丘正在念诵这样一首法句偈: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指出,该比丘将这首偈颂念错了,正确的偈颂应该是: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阿难偈中所讲的“生灭法”,指佛教的基本理论“缘起论”。该比丘把阿难的话告诉自己的师傅,师傅回答:“阿难已经老糊涂了,尽说一些糊涂话。我原来教你的偈颂没有错,你还是依旧修持,不要去理他。”
这段记载说明早在阿难尚在世时期,已经出现对佛典的改篡,阿难虽想纠正,但已无能为力。根据《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当时还有这样的师傅,因为担心弟子掌握佛法后会瞧不起师傅,便故意将三藏经典秘而不宣,不向弟子传授。这样的人自然也会使佛教典籍的传承发生危机。
为了捍卫佛典的权威性与佛教教义的纯洁性,一些教团采用了比较严格的传承制度。《出三藏记集》卷五记述道安的话说:“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摒之,僧法无纵也。”介绍了印度佛教学习佛经的方法。早期到中国来传教的西域僧人,一般都没有携带佛经经本。而是把自己记忆的佛经背诵出来,译为中文。这种方式,也体现了古印度佛经依靠口口相传来流通的传统。当然,佛教经典越来越多,全部靠记忆越来越困难。后来不少教团逐渐把佛典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由此形成所谓“贝叶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