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大荔著名布商——冯翊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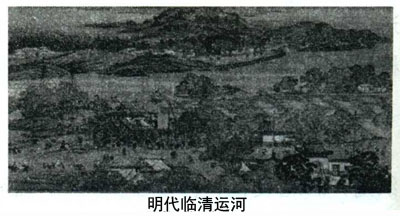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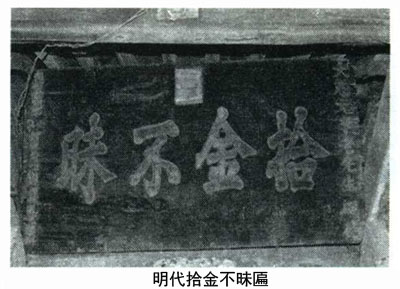

明代陕西布商是陕西商帮的重要力量,他们市驴牵马,泛舸长江,千里奔腾,到江南贩布,形成棉、布对流的东西部贸易流向。其中陕西朝邑(今大荔县)布商冯翊睢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明代布市周转码头临清
明东昌府临清,系漕运五大码头之一。15世纪中叶以后,运河交通日繁,临清人口渐增,弘治二年(1489)由县升为州,又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扩建城垣,增建土城。卫河自南水门入,穿城偏西境曲折北行;汶河(即会通河)自东水门入,至鳌头矶一分为二;其北支西北行,于临清闸与南来之卫河合流北上,即为北运河;其南支过鳌头矶掉头而南,于板闸与卫河交汇。三条水道生机勃勃。土城的五个区,商业均甚繁华。
中州是东西货物水旱码头,“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是临清商业“最为繁盛”①之区。一条长街贯穿南北,自北而南分为锅市街、青碗市街、马市街三段,长达三里有余。锅市街及青碗市街两侧,皮货、冠帽、鞋袜、杂货、米豆、纸张等各类店铺林立,其中瓷器店和纸店最多时都曾达20余家,羊皮店也有七八家之多。马市街主要集中了银钱、皮货、帽靴、海味、果品、杂货等铺。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布匹、绸缎等铺在明代都曾多达数十家。再南为粮食市,有粮店十余家,主要经销自河南卫辉等处运来的粮食。长街尽南端的东、西夹道,“亦为市贾所聚”②。长街以东为榷税分司所在,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验关纳税。
临清城内商业繁华,在当时北方是较少见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市几乎遍布全城。据民国志记载,临清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市肆栉比”③,大小店铺随处可见。如中州的锅市街、青硫街、马市街以及北区的小市街等,均属于百货荟萃的综合性商业街;而白布巷、果子巷、卫河西浒的茶叶店,以及遍布全城六个区的粮食市等,则是以专营某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为特征的商业街区。
第二,店铺种类繁多。上述已经提及的店铺就有数十种,其中包括粮食、布店、绸缎店、丝店、皮货店、羊皮店、鞋袜靴帽店、估衣店、锅店、瓷器店、纸店、金属器皿(如金、银、铜、锡、铁等)铺、烟、酒、茶、盐、果品、海味、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等)、木料、船具、木器、家具、首饰、古玩等各种店铺;碾坊、磨坊、油坊、皮毛加工、竹木作坊等也有一些是带店铺的。此外,还有银钱、典当等铺,焦石木炭店,药材行,饮食店和制作香烛纸马、盆、桶、锅盖等作坊店铺,以及棉花市、绵绸市、线市、姜市、柴市、猪市、鸡鸭市等农副产品的专门市场。可见,城区商业经营的商品门类繁多,档次齐备,可适应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
第三,商店数量众多。据州志记载,乾隆时北区长仅里许的小市街就有商店百余家。以上二者相互参证,可以肯定,明代和清代临清城内店铺的数量起码在五六百家以上,明代则更多些。如果再加上各种类型的集市商贩、作坊店铺,临清的大小商业店铺可能达到千余家。
商品流通当然离不开商人。活跃于临清市场上的商人,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客籍。州志称,临清“本境之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甚至说“逐末者十室而九”。客籍商人有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南京商人,也有来自山陕、辽东、河南、直隶乃至山东本省的济宁、青州、登、莱诸府的商人。州人刘梦阳也说,“临清以聚贾获名”。外来客商是构成临清商人队伍的主体,在临清,外来的商业资本以绸缎、布匹、粮、茶、盐等项的批发中转贸易及银钱典当业为主要经营项目。
以外来客商的活动为中心,在临清形成一整套商业、服务业体系,构成临清城市经济的主体,并左右着本城大部分居民的生计。临清城内虽亦有丝织、皮毛加工等手工业,但与这个庞大的商业经济体系相比,在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甚微。临清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围绕着商品流通这一中心运转的。
在这个南北货物交流的大码头中,陕西布商冯翊睢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贸易故事。
二、冯翊睢的经营故事
冯翊睢的经营情况在明代朝邑文人韩邦奇为其撰写的《冯翊睢公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公讳敖,字大有,少习举子业未就,乃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成化中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任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彼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矣。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公好施,乐成人之美。里之贫不能成婚者,每资给之……公父浩永乐间商于汴洛,拾客百金,客泣寻金欲死,公究客实亡金者,与客金。”④
据此可知,冯翊睢也是少年才俊,从小习儒举业,但多不中,遂弃儒为农服贾。其家为商贾之家,其父冯浩早年经商于汴洛,应为布商。因为明代陕西布客赴江南购布,多走潼关经汴洛的东官道,至卫河之孙家楼弃旱就船,到临清入通济运河到苏杭,这条商道在明代一直是陕西商人赴江南贩布的主干道。直到明末清初,阻挡丹江的巨石被炸毁后,全线通航,才改由长江入汉江、丹江到龙驹寨起旱的水路。冯翊睢随父亲经商于江南塞北之间,有一次过临清,雇伙计到杭州贩布。那时陕西商人做的都是大生意,一个布商一次携带“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⑤,多成为盗贼洗劫的对象。褚华《沪城备考》“神救布商条”载:“万历癸末,邑有新安布商,持银六百两,寄载于田庄船,将往周浦,其银子为舟子所窥,黑夜中,三人共谋,缚客于铁锚,沉之黄浦,而瓜分所有焉。”⑥携带六百两银子都被盗贼所劫,更不用说数十万两,所以成书于明代的《水陆路程》是专为布商们贩运棉布提供的行路指南,该书谓布商“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大仓、燕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棱船,怕风防潮,南翔北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至上海,或遇水涸,七宝、南翔并有骡马而去。港多桥小,雨天难行”⑦,就真实反映了这条商路的凶险。冯翊睢父子在临清贩布时,人生地不熟,误雇佣盗贼为佣,幸亏在一位老者的指点下提前辞退盗贼,才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财去人亡的悲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陕西商人“服远贾”,到天南海北做生意的艰难。
冯翊睢父子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善良诚信。冯翊睢父亲冯浩,诚实忠厚,拾金不昧,急人所难,表现了当年陕西商人良好的经营素质。他在汴洛间做生意,拾百金,这对一个小户经营的商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当时江南一匹标布的购价是7钱银子,到陕西可卖到二三两银子,一般都是3倍的利润,一百金可买百多匹标布,赚到二三百两银子。面对利益的诱惑,冯浩从陕西人忠厚不欺的秉性出发,不为所动,而是急人所难,见到失金者寻金欲死,确认是失主时,将百金还给了失主。这样的拾金不昧故事,在陕西商人中所在多有。这一方面是因为,陕西厚重的黄土地赋予了陕西人厚德载物、诚实醇厚的性格禀赋;另一方面,十三朝文明古都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形成了陕西人“驽而不贪”的价值观念,使陕西人有穿透金钱拜物教的历史灵性。明清时分,陕西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生儿不如我,要钱干什么,生儿胜过我,要钱干什么”,表现了陕西人对金钱的一种超脱潇洒的态度。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冯浩能够急人所难,不取不义之财,拾金不贪,归还失主,表现了良商诚贾的优秀品质。
在冯浩的教导下,冯翊睢继承父志。家道饶裕后,乐善好施,喜成人之美,资助慈善,关怀孤独,乡党中有贫困不能成婚者,他每每慷慨解囊,资给钱财,在乡亲父老中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①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②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建置》。
③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1,《物产志》。
④韩邦奇:《苑洛集》,关中丛书刻本,卷4,第23-24页。
⑤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食货》。
⑥褚华:《沪城备考》,上海申报馆光绪四年刻本,卷6,《杂记》。
⑦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一、明代布市周转码头临清
明东昌府临清,系漕运五大码头之一。15世纪中叶以后,运河交通日繁,临清人口渐增,弘治二年(1489)由县升为州,又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扩建城垣,增建土城。卫河自南水门入,穿城偏西境曲折北行;汶河(即会通河)自东水门入,至鳌头矶一分为二;其北支西北行,于临清闸与南来之卫河合流北上,即为北运河;其南支过鳌头矶掉头而南,于板闸与卫河交汇。三条水道生机勃勃。土城的五个区,商业均甚繁华。
中州是东西货物水旱码头,“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是临清商业“最为繁盛”①之区。一条长街贯穿南北,自北而南分为锅市街、青碗市街、马市街三段,长达三里有余。锅市街及青碗市街两侧,皮货、冠帽、鞋袜、杂货、米豆、纸张等各类店铺林立,其中瓷器店和纸店最多时都曾达20余家,羊皮店也有七八家之多。马市街主要集中了银钱、皮货、帽靴、海味、果品、杂货等铺。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布匹、绸缎等铺在明代都曾多达数十家。再南为粮食市,有粮店十余家,主要经销自河南卫辉等处运来的粮食。长街尽南端的东、西夹道,“亦为市贾所聚”②。长街以东为榷税分司所在,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验关纳税。
临清城内商业繁华,在当时北方是较少见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市几乎遍布全城。据民国志记载,临清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市肆栉比”③,大小店铺随处可见。如中州的锅市街、青硫街、马市街以及北区的小市街等,均属于百货荟萃的综合性商业街;而白布巷、果子巷、卫河西浒的茶叶店,以及遍布全城六个区的粮食市等,则是以专营某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为特征的商业街区。
第二,店铺种类繁多。上述已经提及的店铺就有数十种,其中包括粮食、布店、绸缎店、丝店、皮货店、羊皮店、鞋袜靴帽店、估衣店、锅店、瓷器店、纸店、金属器皿(如金、银、铜、锡、铁等)铺、烟、酒、茶、盐、果品、海味、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等)、木料、船具、木器、家具、首饰、古玩等各种店铺;碾坊、磨坊、油坊、皮毛加工、竹木作坊等也有一些是带店铺的。此外,还有银钱、典当等铺,焦石木炭店,药材行,饮食店和制作香烛纸马、盆、桶、锅盖等作坊店铺,以及棉花市、绵绸市、线市、姜市、柴市、猪市、鸡鸭市等农副产品的专门市场。可见,城区商业经营的商品门类繁多,档次齐备,可适应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
第三,商店数量众多。据州志记载,乾隆时北区长仅里许的小市街就有商店百余家。以上二者相互参证,可以肯定,明代和清代临清城内店铺的数量起码在五六百家以上,明代则更多些。如果再加上各种类型的集市商贩、作坊店铺,临清的大小商业店铺可能达到千余家。
商品流通当然离不开商人。活跃于临清市场上的商人,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客籍。州志称,临清“本境之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甚至说“逐末者十室而九”。客籍商人有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南京商人,也有来自山陕、辽东、河南、直隶乃至山东本省的济宁、青州、登、莱诸府的商人。州人刘梦阳也说,“临清以聚贾获名”。外来客商是构成临清商人队伍的主体,在临清,外来的商业资本以绸缎、布匹、粮、茶、盐等项的批发中转贸易及银钱典当业为主要经营项目。
以外来客商的活动为中心,在临清形成一整套商业、服务业体系,构成临清城市经济的主体,并左右着本城大部分居民的生计。临清城内虽亦有丝织、皮毛加工等手工业,但与这个庞大的商业经济体系相比,在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甚微。临清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围绕着商品流通这一中心运转的。
在这个南北货物交流的大码头中,陕西布商冯翊睢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贸易故事。
二、冯翊睢的经营故事
冯翊睢的经营情况在明代朝邑文人韩邦奇为其撰写的《冯翊睢公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公讳敖,字大有,少习举子业未就,乃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成化中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任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彼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矣。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公好施,乐成人之美。里之贫不能成婚者,每资给之……公父浩永乐间商于汴洛,拾客百金,客泣寻金欲死,公究客实亡金者,与客金。”④
据此可知,冯翊睢也是少年才俊,从小习儒举业,但多不中,遂弃儒为农服贾。其家为商贾之家,其父冯浩早年经商于汴洛,应为布商。因为明代陕西布客赴江南购布,多走潼关经汴洛的东官道,至卫河之孙家楼弃旱就船,到临清入通济运河到苏杭,这条商道在明代一直是陕西商人赴江南贩布的主干道。直到明末清初,阻挡丹江的巨石被炸毁后,全线通航,才改由长江入汉江、丹江到龙驹寨起旱的水路。冯翊睢随父亲经商于江南塞北之间,有一次过临清,雇伙计到杭州贩布。那时陕西商人做的都是大生意,一个布商一次携带“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⑤,多成为盗贼洗劫的对象。褚华《沪城备考》“神救布商条”载:“万历癸末,邑有新安布商,持银六百两,寄载于田庄船,将往周浦,其银子为舟子所窥,黑夜中,三人共谋,缚客于铁锚,沉之黄浦,而瓜分所有焉。”⑥携带六百两银子都被盗贼所劫,更不用说数十万两,所以成书于明代的《水陆路程》是专为布商们贩运棉布提供的行路指南,该书谓布商“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大仓、燕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棱船,怕风防潮,南翔北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至上海,或遇水涸,七宝、南翔并有骡马而去。港多桥小,雨天难行”⑦,就真实反映了这条商路的凶险。冯翊睢父子在临清贩布时,人生地不熟,误雇佣盗贼为佣,幸亏在一位老者的指点下提前辞退盗贼,才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财去人亡的悲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陕西商人“服远贾”,到天南海北做生意的艰难。
冯翊睢父子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善良诚信。冯翊睢父亲冯浩,诚实忠厚,拾金不昧,急人所难,表现了当年陕西商人良好的经营素质。他在汴洛间做生意,拾百金,这对一个小户经营的商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当时江南一匹标布的购价是7钱银子,到陕西可卖到二三两银子,一般都是3倍的利润,一百金可买百多匹标布,赚到二三百两银子。面对利益的诱惑,冯浩从陕西人忠厚不欺的秉性出发,不为所动,而是急人所难,见到失金者寻金欲死,确认是失主时,将百金还给了失主。这样的拾金不昧故事,在陕西商人中所在多有。这一方面是因为,陕西厚重的黄土地赋予了陕西人厚德载物、诚实醇厚的性格禀赋;另一方面,十三朝文明古都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形成了陕西人“驽而不贪”的价值观念,使陕西人有穿透金钱拜物教的历史灵性。明清时分,陕西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生儿不如我,要钱干什么,生儿胜过我,要钱干什么”,表现了陕西人对金钱的一种超脱潇洒的态度。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冯浩能够急人所难,不取不义之财,拾金不贪,归还失主,表现了良商诚贾的优秀品质。
在冯浩的教导下,冯翊睢继承父志。家道饶裕后,乐善好施,喜成人之美,资助慈善,关怀孤独,乡党中有贫困不能成婚者,他每每慷慨解囊,资给钱财,在乡亲父老中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①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②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建置》。
③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1,《物产志》。
④韩邦奇:《苑洛集》,关中丛书刻本,卷4,第23-24页。
⑤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食货》。
⑥褚华:《沪城备考》,上海申报馆光绪四年刻本,卷6,《杂记》。
⑦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