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驽而不贪的长安商人——张通、马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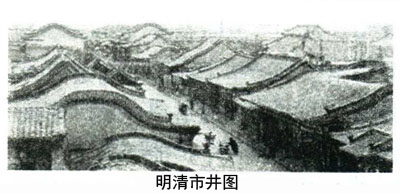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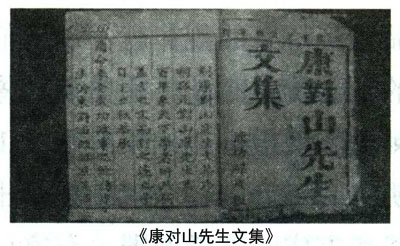
在以利益为驱动的商品经济社会里,追求利益至上或者唯利是图,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建立在亲情血缘关系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使社会陷入“一切向钱看”的泥沼之中。在这种社会风气中,能够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已属难得,更何况取之有度、驽而不贪。而明清的中国商界,陕西商人便能恪守传统道德底线,坚守不贪婪,表现了很高的职业自觉和行为操守。他们中的代表就是长安商人张通和马伦。
一、明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初步转型
明代万历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初步转型期,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从而使传统商业经营意识也发生了三方面的逆转。
一是商业经营目的从“利义兼得”转向“唯利是图”。在宋元以前,中国传统商人还能够在社会主流道德引导下,通过商业经营技巧贩贱鬻贵,贱买贵卖,赚取不同经济区之间的地区差价和同一商品的供求和质量差价的合理利润,在汉武帝“告缗”运动的教训和打击下,商人们还能坚持以义取利的主流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上以利人,下以利己”,将商业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联系,尚不因谋利而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明清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产生,人们从过去追求使用价值为目的,开始转变为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对财富的占有不再受自身消费力的限制,占有货币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明代在追求货币无限增值利益驱动下,为获取赢利,赚钱发财,商人的灵魂被扭曲,使商人开始抛弃社会良知,“富人无不起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骛奔走,竟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①明清小说《今古奇观》“徐老仆义愤成家”借商人之口将商人求利的目的说得很直白:“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②
二是商业操作方式从“阳光经营”转向“暗箱操作”。在宋元以前商人们的商场操作还能坚持“实事求是”③的阳光经营。商鞅是先秦商人的著名代表,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竖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五十。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他即当众赏五十金,以示不欺。④宋以后,在市场经济因素的利益驱动下,社会开始陷入对价值增值疯狂的追求,一部分商人发生灵魂的嬗变,追求利润已经达到不顾礼义廉耻的程度。
三是官商关系从“不相交接”转向“官商勾结”。在宋元以前,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分层和官府的“贱商”高压政策,使官员与商人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虽说从齐国管仲“官盐铁”以来,政府对盐铁等生利事业实行专卖,但那是政府有组织的行为,官员个人经商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社会职业目标分层的指向下,为社会所不齿。汉代文人杨恽就记载了自己经商的亲身体会,他在《报孙会宗书》中说:“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侮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⑤官商之间还能维持一种“不相交接”、“各行其道”的清明状态。明清以后,在利益驱动的刺激下,全社会弥漫着逐利的风气,士农工商职业分层的固态被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所打破,士的向下移动与商的向上移动杂糅交错,互相交叉。在学而优则仕,因官员职数有限被堵塞后,一部分儒生开始抛弃“不言利”的清高虚饰而转向“弃儒经商”。而官员在利润刺激下,利用手中的权力纷纷下海经商,与民争利,上至皇室贵戚,下至书吏皂隶,莫不以权子母为念,许多官员寡廉鲜耻,将仕途作为钱权交易的筹码,公然渔利,“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交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⑥,衙门几与市场无异。而商人为逃避官府需索,亦需要借官府之威以为保护,也纷纷通过捐纳卖官鬻爵,为其子弟求得一官半职,使“商道”与“官道”交织重叠,商道胶合了官道的“尔虞我诈”,更加阴暗多蹇;官道汲取了商道的唯利是图,更加贪得无厌,社会呈现出官商上下交乘、盘剥渔利的邪恶风气。
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趋利经济。传统社会一旦转向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发挥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判断。原先那种停滞的固态的社会,在价值规律的效益最大化刺激和两极分化结果的作用下,呈现出变异的、流动的社会。有记载说,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现状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到了明代末期,更是“资爱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周极,骨肉相残”⑦,以至于有人惊呼:“天道变迁,人事亦改。”⑧这正是对社会转型时期变化的一种十分准确的惊叹。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在坚持取得合理利润的同时恪守“驽而不贪”的道德底线,充分展现传统商人高风亮节的正是明代陕西长安商人张通和马伦。
二、张通、马伦的经营事迹
张通的经营事迹在明武功文人康海为其撰写的《明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掌柜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公讳通,字大亨,家世长安杜陵人……自家道少衰,乃令就贾……贾不数年,其足迹已遍天下,而诸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矣。然公性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⑨
马伦的经营事迹在康海为其撰写的《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马公墓志铭》中也有记载:
“公马姓,讳伦……世为西安人……公亲爰畜产而家或不丰,于是以所有易马货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自笑曰,财取足用而已,役之于此,不亦苦乎,亦弃业不为。”⑩
张通与马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取用有度、节缩自觉、驽而不贪。尽管他们都是经商求财,张通是因为“家道少衰”才走上经商道路;马伦是因为“家或不丰”才易马求财。但他们都是经商奇才,张通“贾不数年,其足迹已遍天下,而诸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矣”,足见其生意做得很大,成为那一时期的陕商领袖;马伦是倾其所有,贩马致富。可他们致富后有一个共同的取舍,就是将经商的目的放在满足生活需求的节点之上,不刻意求取太多的价值和利润,以求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张通是“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他认为经商求利是“生道所关”,本身并无可非议,是正当自觉的社会行为。但在求富的过程中,要节缩有度,不能贪得无厌,这个度就是“苟可以给日用”,满足自身的生活所需,过上富裕的生活。那种无限制地追求利益,无限制地向自然和社会索取是不可取的,是没有发展眼光的,“夫何以厚为哉”。马伦比张通走得更远。他发家后,幡然有悟,认为经商业贾就是“财取足用而已”,满足生活的富足,超过了这一点,做过度的利益追求是“不亦苦乎”,自找苦吃,得不偿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宁可“弃业不为”,表现了对财富索取和占有上的一种知足常乐、潇洒自如的认知和情态。这种取用有度、驽而不贪的价值取向,并不是陕西商人的惺惺作态,而是有着他们对自然和社会更深层次的认识。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的初期大多数是从农民转化而来,他们并没有割断与农业生产的联系,他们对等能量转换规律对他们影响很深,对利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对逐利的职业目标有一种无法超越的中世纪温情,更注重处理逐利过程中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经商逐利与生命本善相联系,使商业经营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山陕商人有一篇有名的《省份箴》,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商人对生活、对世界、对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展示了中国传统商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对生活游刃有余的超脱心态,不知要比西方商人的冷酷理性高明多少倍。该《省份箴》这样写道:
“久晦昼明,乾动坤静。物秉乎性,人贱乎命。贵贱贤愚,寿天衰盛。谅夫自冥数潜定。葱生数寸,松高百尺。水润火炎,轮曲辕轴。或金或锡,或玉或银。茶苦芥甘,乌墨鹭白,体不可移。揠苗则猝,续袅乃悲。巢者罔穴,诈者宁驰。竹柏寒茂,桐柳黔秋。健美勿用,止足尚可。处安顺时,右路长昌。”(11)
徽商程春宇的《士商类要》中也倡导“致中和”之道,认为“人过者,满则必倾,执中者,平而且稳”,指出“凡人存心处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倘遇势穷财尽,祸害临身,四面皆仇敌矣。惟能处势益谦,处财益宽,处能益逊,处仇益德。若然,不独怀人以德,足为保身保家之良策也”。(12)
这些认知充分表露了中国传统商人道法自然,止足尚可,驽而不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儒家“中庸之道”对中国传统商人的灵魂洗礼。它使中国传统商人能够形成“知足不贪”的价值诉求,其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说明中国传统商人对世界、对人生的认知和理解远比西方利己学说高明而深刻。
无独有偶,明代河南与江苏沈(百万)万三、山西“亢百万”齐名的巨商康百万,在自己的庄园中也留下了一篇《留余匾》,与山陕商人的《省份箴》一样,道出了中国传统商人共同的心曲。
“留耕道人《留余匾》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利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钱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事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13)
这是中国传统商人对“满则虚”、“盈则亏”生活辩证法的深层次理解,也是中国传统商人以人为本“利润观”的坦然表露,表现了传统商人已经懂得“爱别人就是爱自己”的以人为本深层哲学思维。
明清的陕西商人做生意驽而不贪,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理性。陕西是中国道教的发祥之地,道教的“戒贪”、“无为”对陕商有很深刻的教化。陕西周至县赵大村中华正财神赵公明故里的财神殿有一副楹联表达了陕西商人的仁义知足理念:“生财有大道,则拳拳服膺,仁也是,义也是,富哉言乎至足矣;君子无所争,故源源而来,孰与之,天与之,神之格思如是夫。”(14)所以,驽而不贪,见好就收,让利双赢,讲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就是陕西商人的常胜法则。
①雍正《安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俗》。
②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卷25。
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53,《河间献王刘德传》。
④《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⑤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66,《杨恽传》。
⑥李乐:《续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4。
⑦万历:《歙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土》。
⑧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2。
⑨康海:《康对山文集》,关中丛书本,卷6,第6页。
⑩康海:《康对山文集》,关中丛书本,卷6,第4页。
(11)王先明:《晋中大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12)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献》1990年第2期。
(13)陈义初:《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妙》,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4)张怀庆:《楼观怀想》,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一、明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初步转型
明代万历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初步转型期,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从而使传统商业经营意识也发生了三方面的逆转。
一是商业经营目的从“利义兼得”转向“唯利是图”。在宋元以前,中国传统商人还能够在社会主流道德引导下,通过商业经营技巧贩贱鬻贵,贱买贵卖,赚取不同经济区之间的地区差价和同一商品的供求和质量差价的合理利润,在汉武帝“告缗”运动的教训和打击下,商人们还能坚持以义取利的主流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上以利人,下以利己”,将商业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联系,尚不因谋利而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明清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产生,人们从过去追求使用价值为目的,开始转变为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对财富的占有不再受自身消费力的限制,占有货币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明代在追求货币无限增值利益驱动下,为获取赢利,赚钱发财,商人的灵魂被扭曲,使商人开始抛弃社会良知,“富人无不起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骛奔走,竟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①明清小说《今古奇观》“徐老仆义愤成家”借商人之口将商人求利的目的说得很直白:“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②
二是商业操作方式从“阳光经营”转向“暗箱操作”。在宋元以前商人们的商场操作还能坚持“实事求是”③的阳光经营。商鞅是先秦商人的著名代表,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竖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五十。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他即当众赏五十金,以示不欺。④宋以后,在市场经济因素的利益驱动下,社会开始陷入对价值增值疯狂的追求,一部分商人发生灵魂的嬗变,追求利润已经达到不顾礼义廉耻的程度。
三是官商关系从“不相交接”转向“官商勾结”。在宋元以前,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分层和官府的“贱商”高压政策,使官员与商人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虽说从齐国管仲“官盐铁”以来,政府对盐铁等生利事业实行专卖,但那是政府有组织的行为,官员个人经商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社会职业目标分层的指向下,为社会所不齿。汉代文人杨恽就记载了自己经商的亲身体会,他在《报孙会宗书》中说:“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侮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⑤官商之间还能维持一种“不相交接”、“各行其道”的清明状态。明清以后,在利益驱动的刺激下,全社会弥漫着逐利的风气,士农工商职业分层的固态被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所打破,士的向下移动与商的向上移动杂糅交错,互相交叉。在学而优则仕,因官员职数有限被堵塞后,一部分儒生开始抛弃“不言利”的清高虚饰而转向“弃儒经商”。而官员在利润刺激下,利用手中的权力纷纷下海经商,与民争利,上至皇室贵戚,下至书吏皂隶,莫不以权子母为念,许多官员寡廉鲜耻,将仕途作为钱权交易的筹码,公然渔利,“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交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⑥,衙门几与市场无异。而商人为逃避官府需索,亦需要借官府之威以为保护,也纷纷通过捐纳卖官鬻爵,为其子弟求得一官半职,使“商道”与“官道”交织重叠,商道胶合了官道的“尔虞我诈”,更加阴暗多蹇;官道汲取了商道的唯利是图,更加贪得无厌,社会呈现出官商上下交乘、盘剥渔利的邪恶风气。
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趋利经济。传统社会一旦转向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发挥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判断。原先那种停滞的固态的社会,在价值规律的效益最大化刺激和两极分化结果的作用下,呈现出变异的、流动的社会。有记载说,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现状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到了明代末期,更是“资爱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周极,骨肉相残”⑦,以至于有人惊呼:“天道变迁,人事亦改。”⑧这正是对社会转型时期变化的一种十分准确的惊叹。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在坚持取得合理利润的同时恪守“驽而不贪”的道德底线,充分展现传统商人高风亮节的正是明代陕西长安商人张通和马伦。
二、张通、马伦的经营事迹
张通的经营事迹在明武功文人康海为其撰写的《明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掌柜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公讳通,字大亨,家世长安杜陵人……自家道少衰,乃令就贾……贾不数年,其足迹已遍天下,而诸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矣。然公性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⑨
马伦的经营事迹在康海为其撰写的《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马公墓志铭》中也有记载:
“公马姓,讳伦……世为西安人……公亲爰畜产而家或不丰,于是以所有易马货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自笑曰,财取足用而已,役之于此,不亦苦乎,亦弃业不为。”⑩
张通与马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取用有度、节缩自觉、驽而不贪。尽管他们都是经商求财,张通是因为“家道少衰”才走上经商道路;马伦是因为“家或不丰”才易马求财。但他们都是经商奇才,张通“贾不数年,其足迹已遍天下,而诸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矣”,足见其生意做得很大,成为那一时期的陕商领袖;马伦是倾其所有,贩马致富。可他们致富后有一个共同的取舍,就是将经商的目的放在满足生活需求的节点之上,不刻意求取太多的价值和利润,以求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张通是“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他认为经商求利是“生道所关”,本身并无可非议,是正当自觉的社会行为。但在求富的过程中,要节缩有度,不能贪得无厌,这个度就是“苟可以给日用”,满足自身的生活所需,过上富裕的生活。那种无限制地追求利益,无限制地向自然和社会索取是不可取的,是没有发展眼光的,“夫何以厚为哉”。马伦比张通走得更远。他发家后,幡然有悟,认为经商业贾就是“财取足用而已”,满足生活的富足,超过了这一点,做过度的利益追求是“不亦苦乎”,自找苦吃,得不偿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宁可“弃业不为”,表现了对财富索取和占有上的一种知足常乐、潇洒自如的认知和情态。这种取用有度、驽而不贪的价值取向,并不是陕西商人的惺惺作态,而是有着他们对自然和社会更深层次的认识。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的初期大多数是从农民转化而来,他们并没有割断与农业生产的联系,他们对等能量转换规律对他们影响很深,对利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对逐利的职业目标有一种无法超越的中世纪温情,更注重处理逐利过程中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经商逐利与生命本善相联系,使商业经营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山陕商人有一篇有名的《省份箴》,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商人对生活、对世界、对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展示了中国传统商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对生活游刃有余的超脱心态,不知要比西方商人的冷酷理性高明多少倍。该《省份箴》这样写道:
“久晦昼明,乾动坤静。物秉乎性,人贱乎命。贵贱贤愚,寿天衰盛。谅夫自冥数潜定。葱生数寸,松高百尺。水润火炎,轮曲辕轴。或金或锡,或玉或银。茶苦芥甘,乌墨鹭白,体不可移。揠苗则猝,续袅乃悲。巢者罔穴,诈者宁驰。竹柏寒茂,桐柳黔秋。健美勿用,止足尚可。处安顺时,右路长昌。”(11)
徽商程春宇的《士商类要》中也倡导“致中和”之道,认为“人过者,满则必倾,执中者,平而且稳”,指出“凡人存心处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倘遇势穷财尽,祸害临身,四面皆仇敌矣。惟能处势益谦,处财益宽,处能益逊,处仇益德。若然,不独怀人以德,足为保身保家之良策也”。(12)
这些认知充分表露了中国传统商人道法自然,止足尚可,驽而不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儒家“中庸之道”对中国传统商人的灵魂洗礼。它使中国传统商人能够形成“知足不贪”的价值诉求,其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说明中国传统商人对世界、对人生的认知和理解远比西方利己学说高明而深刻。
无独有偶,明代河南与江苏沈(百万)万三、山西“亢百万”齐名的巨商康百万,在自己的庄园中也留下了一篇《留余匾》,与山陕商人的《省份箴》一样,道出了中国传统商人共同的心曲。
“留耕道人《留余匾》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利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钱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事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13)
这是中国传统商人对“满则虚”、“盈则亏”生活辩证法的深层次理解,也是中国传统商人以人为本“利润观”的坦然表露,表现了传统商人已经懂得“爱别人就是爱自己”的以人为本深层哲学思维。
明清的陕西商人做生意驽而不贪,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理性。陕西是中国道教的发祥之地,道教的“戒贪”、“无为”对陕商有很深刻的教化。陕西周至县赵大村中华正财神赵公明故里的财神殿有一副楹联表达了陕西商人的仁义知足理念:“生财有大道,则拳拳服膺,仁也是,义也是,富哉言乎至足矣;君子无所争,故源源而来,孰与之,天与之,神之格思如是夫。”(14)所以,驽而不贪,见好就收,让利双赢,讲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就是陕西商人的常胜法则。
①雍正《安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俗》。
②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卷25。
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53,《河间献王刘德传》。
④《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⑤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66,《杨恽传》。
⑥李乐:《续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4。
⑦万历:《歙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土》。
⑧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2。
⑨康海:《康对山文集》,关中丛书本,卷6,第6页。
⑩康海:《康对山文集》,关中丛书本,卷6,第4页。
(11)王先明:《晋中大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12)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献》1990年第2期。
(13)陈义初:《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妙》,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4)张怀庆:《楼观怀想》,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