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关中以商求富的代表——李鸿虞、张云宵、樊现、张忠轩和王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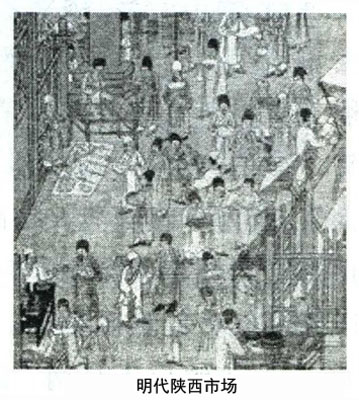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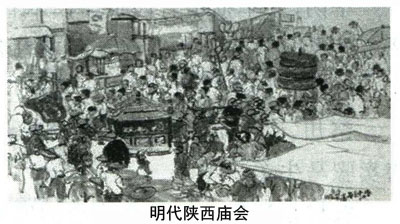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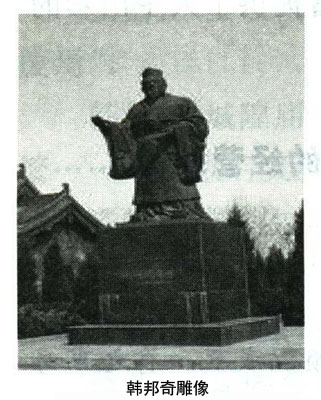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经商业贾常常是人们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路径之一。明代的关中,就有不少通过经商而打开财富之门的著名商人,李鸿虞、张云宵、樊现、张忠轩和王舆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明代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在明清时期,我国的市场贸易从以奢侈品为主开始转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逐渐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唐宋时期,市场流通主要是为达官贵人服务,唐元稹《估客乐》诗中描绘陕西商人做生意的情形是“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土蕃鹰,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遍天下,却到长安城……先问十常待,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①。到明清后,由于农村商品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日益频繁,使民生日用、奉生送死的生活用品逐渐成为交换的主体,这种因民间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民生日用品大量进入流通,必然有力推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容量的加深。
明清陕西市场范围的扩大,首先表现为农村集市贸易的扩展和繁盛。集市贸易是适应农村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形成的初级市场。集市一般特点是“市廛有地,交易有期”②,交换以当地产品为主,须逢场期,始来交易,平时市面冷落,故有谚曰“聚者为集,散者为墟”。集的分布以方圆十余里为度,保证农民一日步行,可以来回,以便不误农时。明清陕西集市的设立,可以明代临潼广阳新市为例,“广阳故无市,有之,自万历乙未始也。镇界在清沮河之间。而河四面环绕如带,中数十里之地,居民萃止,称隩区焉。而苦无市值贸易,即一丝麻布缕之属,辄赴河外诸镇。迟或不及为五都之观,早则为暴客御之于途……是河内数十里之不可无市,而河内数十里之民无日不思为市甚殷也……广阳为两河中地,四方辐辏实便也。乃相率请之于邑侯马公,公是请,为投牒立课,是视镇矣。”③
定期的年会、庙会、古会是集市贸易的另一种形式,旧志云“凡买卖牲口之期曰会,糶籴米粮之期曰集”。《陕西通志稿》亦指出:“陕右赛会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所以通省皆有集场。”④年会、庙会一般与农村节令和生产季节相联系,或为农耕准备,如泾阳鲁桥之四月上旬“显佑神会”,山阳四月廿八日之“浴佛大会”,定边三九月之“牲畜会”;或为丰收庆典,如高陵之“冬至之会”,三原正月“灯山会”,省垣正月之“城隍庙会”。年会、庙会期间往往“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呈现繁盛红火的热闹场面。可以洛川“石头镇大会”和三原“腊八会”为例:“石头镇位于县南,距城一百华里,北通榆绥,南达华豫,为商旅往来必经要道。此镇集会历史悠久,甲于陕北。昔每年阴历十月初十至二十日为集会期……相传往昔,马恒以数千计,羊则过万头,家用什物,农工器具,无不全备。参加人数昔时不下2万人,常年约5~6千人参加。每年由驻镇农商八人为会长,筹备集会事宜,戏剧昔时1~2台,于会期前一日开演,借招客商并做酬神报赛,其戏资由商捐集,不足则住户分筹……互通南北商品,物尽其流。”⑤而三原的“腊八会”更被称为“千年古会”、“关中第一大集”。腊八会每年“腊月初八”开会,小年腊月二十三结束。占地二三百亩,届时商贾云集、万人聚会、盛况壮观,会场按行业扎设棚帐,自成巷街,纵横交错,坐落有序,南北各货,应有尽有,其中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群马结帮而来,日上市数以千计,为省内最大的牲畜市场。⑥在明清陕西农村,由于交换发达,庙会成为社区行为,往往各村轮流办会,使庙会成为“村村有会,月月有会”的经常性交易行为。
在明清,陕西庙会的繁盛不仅表现在村村有会,而且表现在县县有会,各县的庙会更是盛况空前。可将《陕西通志稿》所记述的各县“赛会”情况摘录如下:
长安、咸宁,“有赛会四,而以四月初八等日都城隍会为最大,商货联集,蔚成巨观”。
兴平,“城内乡人七行逢会之日,行头倡办演戏各费,西南两街均四月,东街三月二十八日,北街二月十二日,外镇如马嵬二月大会七日,店张十二月大会十日,商旅皆来,杂货交易,延展时日”。
高陵,“冬至之会……商贩云集,严如货市,牛马估衣行木各器皆居多数,棚帐互支,经月始散。
泾阳,“鲁桥镇显佑神会,各演戏数日,商贾贩运估衣京货竹器农具木料及牲畜等类,云集贸易”。
富平,“东乡卤泊湖滩以三月十五日商贾云集,百货具备”。
耀州,“二月大会于城东五台山,八月大会于城内南街……商贾云集,杂货畅销”。
镇安,“城隍庙祀神赛会,阖邑奔走,外境商贩亦纷至沓来,扰扰经旬”。
山阳,“浴佛大会,商贾云集,买卖牛马及雨笠锨帚等物,以名农会”。
商县,“有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众,会中多卖农具布疋”。
大荔,“虽以祀神为宗旨而民间借此置买牲畜器具,行之永久,不能废焉”。
韩城,“城隍庙向立有赛会,当道咸承平时,招致外来商贾,极为殷繁……十五以后又移至西乡沟北村,穑事告成,报赛田祖,是时或市牛马,资耕耨或购衣褐,谋卒岁,或抱布贸丝,以有易无”。
华阴,“华狱镇有西狱会,本省京货估衣及外省州县药材各行皆至,搭盖席棚,售买货物并有花马骡马各市约二十余日乃散”。
凤翔,“城隍冬会,演戏数台,狭旬斗聚山积,珍货谷量马牛”。
洛川,“县城三会,粟米交易,县东黄龙山六月九月有会,稍盛,售卖骡马牛羊”。⑦
农村定期集市贸易和庙会的发展,要求打破交换所受到的时间性限制,推动着交换与集镇的常住人口的结合,导致集镇合而为一,产生和发展了比农村集市贸易初级市场更进一步的市镇。在明清的陕西农村,随民间商品流通的兴盛,市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以渭南县明清市镇的消长变化为例:明代嘉靖年间,渭南有市镇16个;到雍正十二年,市镇增加到30个,与明代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到光绪十八年,市镇又增到36个。⑧许多市镇成为著名的农村工商业中心,如户县之秦渡镇,“商贾辐辏,为邑中最盛”⑨,“周围几十里路以内又无大的集镇,每逢集日,商贾云集”⑩;三原陂西镇,“市廛稠密,基砋广袤为邑首镇”(11);朝邑之赵渡镇,“邑名地也,烟户辐辏,被服济楚”(12),“滨渭河,为商贾辐集之所”(13);渭南之孝义镇,“为渭南河北之要区……林木葱茏,人烟稠密,百货聚集其间者,极晦明风雨之无阻,人语喧哗之遥闻,城市之繁庶他属莫能与并”(14);朝邑之赵渡镇,“邑之为市者以十数,而赵渡为最大商贾辐辏,里中一浩穣也,盖称曰市焉”(15);乾县之冯市镇,“为商贾走集之所”(16);甘泉的临直镇,“居民富庶,为县大镇”(17);宜君之百直镇,“为商贾辐辏之所”;保安县之沙家镇,“为商贾往来贸易之地也”(18)。
明代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为人们经商致富提供了人生出彩的舞台。
二、李鸿虞、张忠轩、樊现、张云宵和王舆的经营过程
李鸿虞是泾阳人,他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文人温自知为其撰写的《明故公李鸿虞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鸿虞李翁,幼令丧父,有母尸饔,拘劳万状,赖以成立。翁之事母恪尽孝道,翁习计然之策,遂成良贾,万货之情,亿则屡中,知人而时使之,克勤克俭,居积致富。”成为泾阳“东郭巨族”。(19)
张忠轩是高陵人,他的经营事迹在《张忠轩合葬墓志铭》中有记载:
“处士张公……初业儒……且家贫,菽水不充……遂纯艺黍稷,肇牵牛车,登临巩涉泗水,以图洗腆,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即古之托畎亩鱼盐海市者也。”(20)
樊现是扶风人,他的经营事迹在康海为其撰写的《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樊翁早年丧母,后又为继母所逐,近有破房半间。但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勤俭持家,数年家有中人之产,先走南闯北,以经商成巨富,积赀弥万。”(21)
张云霄是朝邑人,他的经营事迹在渭南文人韩邦奇为其撰写的《张云霄墓志铭》中有记载:
“云霄世为朝邑大庆关人,自祖父来以赀雄于关……张氏毁于盗,赀产几尽……云霄乃舟自刻历,尽反旧好,不数年家至几万金。”(22)
王舆是泾阳人,他的经营事迹在户县文人王九思为其撰写的《明故秦府良医王君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王舆经商发财后,回家买田,“君当此郭买田数亩。创作别业,植花卉竹林。有水有亭,奉其父母居之。比葬母后,日与朋旧高会于此,二子俱成立,又抱孙,而家道甚备,始无意于江湖之迹,其乐陶陶。”(23)
他们五人都是因为经商而脱贫致富,又都因为经商而保持了商人优秀的品质。
李鸿虞是因为习计然之策,靠自己的经营智慧,“万货之情,臆则屡中”,克勤克俭,成为泾阳“东郭巨族”;张忠轩是力农积粟,将农业上的积蓄转化为商业投资,又肯吃苦耐劳,肇牵牛车,经商足迹遍及天南海北,实行农业与商业互相支撑的经营策略,“即古之托畎亩鱼盐海市者也”,取得经营的成功;樊现从破房半间起家,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勤俭持家,从小本经营做起,借他姐姐的嫁妆为资本,走上大规模涉外经营的道路,“走南闯北,以经商成巨富,积赀弥万”;张云霄虽说是商贾之家,但家道几起几落,多亏张云霄“舟自刻历”,逆境奋起,不屈不挠地努力经营,“不数年家至几万金”;王舆是经商发家,然后置田起屋,“其乐陶陶”享受创业成功的乐趣。他们的生活经历证明了“勤奋劳动致富,合法经营发家”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但是,他们发家致富后,并没有奢侈靡费、横行乡里、恃才傲物,而是保持着陕西人节俭内敛的生活作风,保持着优秀商人的品质和修养。李鸿虞是发家后“恪尽孝道”、“克勤克俭”,保持着勤劳动经营作风;张忠轩更是文人下海经商,“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保持着“儒商”的高雅情态;樊现是小本经济起家,发财后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夫妻二人克勤克俭,不忘创业之艰难;张云霄是几经阀阅,经历千辛万苦,才重振家声,因他保持着良好的经营作风,结缘各方,人们认可他的人品,才“尽反旧好”,帮助他渡过难关,梅开二度;王舆是发家后,起华屋孝敬父母,并交结好友,乐施乡邻,才得以尽享晚年的亲情之乐。这些也都说明保持优秀商人的品质、不轻狂张扬、内敛自省、结缘各方是商业经营长兴不衰的社会法则。
同时,他们的成功也说明以贫求富,仅靠吃苦耐劳是不够的。商海无涯,风波骤起,要在充满风险的商海中扬帆远航,还要依靠自身的经营智慧,按照商业经营规律办事,才能获得预期的经营效果。李鸿虞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认真学习商业经营经验,仔细把握商业的供求变化规律,以销定货,趋市供应,做到了“万货之情,臆则屡中”,而且知人善任,设法调动伙计的积极性,才取得了成功;张忠轩更是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商业实践中,用知识指导商业经营,“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保持着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表现了优秀商人的高贵品质;樊现是贩夫贩妇,肖小起家,丈夫走南闯北于外,妻子勤俭持家于内,夫妻共同戮力,才赚得了偌大的家私;张云霄是不畏艰难,“舟自刻历”,满怀逆境不弃的勇气,用自己良好的道德修养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可和周济,才取得了两度创业的成功。这些也都说明在经商致富的道路上,“有力吃力,无力吃智”、“商以察尽财”、“贾以智求富”是商业活动历久不衰的经济法则。
①元稹:《元氏长庆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卷33。
②乾隆:《富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卷2。
③武之望:《广阳镇新市碑记》,见《临潼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④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陕西通志馆本,卷198,《岁时》。
⑤《陕行汇刊》卷8,第2期。
⑥三原县志办:《三原工商行政管理志》,油印本。
⑦均见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陕西通志馆本,卷198,《岁时》,第24-30页。
⑧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第11页。
⑨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2页。
⑩户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户县文史资料》第4辑,第8页。
(11)三原县商业局:《三原县商业志》油印本,第7页。
(12)李天受:《来紫堂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卷1,第25页。
(13)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4页。
(14)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卷10,《艺文志》。
(15)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9页。
(16)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9页。
(17)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7页。
(18)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8页。
(19)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关中丛书本,卷2。
(20)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87页。
(21)康海:《康对山文集》,关中丛书本,卷38。
(22)韩邦奇:《苑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卷6,第15页。
(23)王九思:《渼陂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14。
一、明代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在明清时期,我国的市场贸易从以奢侈品为主开始转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逐渐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唐宋时期,市场流通主要是为达官贵人服务,唐元稹《估客乐》诗中描绘陕西商人做生意的情形是“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土蕃鹰,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遍天下,却到长安城……先问十常待,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①。到明清后,由于农村商品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日益频繁,使民生日用、奉生送死的生活用品逐渐成为交换的主体,这种因民间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民生日用品大量进入流通,必然有力推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容量的加深。
明清陕西市场范围的扩大,首先表现为农村集市贸易的扩展和繁盛。集市贸易是适应农村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形成的初级市场。集市一般特点是“市廛有地,交易有期”②,交换以当地产品为主,须逢场期,始来交易,平时市面冷落,故有谚曰“聚者为集,散者为墟”。集的分布以方圆十余里为度,保证农民一日步行,可以来回,以便不误农时。明清陕西集市的设立,可以明代临潼广阳新市为例,“广阳故无市,有之,自万历乙未始也。镇界在清沮河之间。而河四面环绕如带,中数十里之地,居民萃止,称隩区焉。而苦无市值贸易,即一丝麻布缕之属,辄赴河外诸镇。迟或不及为五都之观,早则为暴客御之于途……是河内数十里之不可无市,而河内数十里之民无日不思为市甚殷也……广阳为两河中地,四方辐辏实便也。乃相率请之于邑侯马公,公是请,为投牒立课,是视镇矣。”③
定期的年会、庙会、古会是集市贸易的另一种形式,旧志云“凡买卖牲口之期曰会,糶籴米粮之期曰集”。《陕西通志稿》亦指出:“陕右赛会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所以通省皆有集场。”④年会、庙会一般与农村节令和生产季节相联系,或为农耕准备,如泾阳鲁桥之四月上旬“显佑神会”,山阳四月廿八日之“浴佛大会”,定边三九月之“牲畜会”;或为丰收庆典,如高陵之“冬至之会”,三原正月“灯山会”,省垣正月之“城隍庙会”。年会、庙会期间往往“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呈现繁盛红火的热闹场面。可以洛川“石头镇大会”和三原“腊八会”为例:“石头镇位于县南,距城一百华里,北通榆绥,南达华豫,为商旅往来必经要道。此镇集会历史悠久,甲于陕北。昔每年阴历十月初十至二十日为集会期……相传往昔,马恒以数千计,羊则过万头,家用什物,农工器具,无不全备。参加人数昔时不下2万人,常年约5~6千人参加。每年由驻镇农商八人为会长,筹备集会事宜,戏剧昔时1~2台,于会期前一日开演,借招客商并做酬神报赛,其戏资由商捐集,不足则住户分筹……互通南北商品,物尽其流。”⑤而三原的“腊八会”更被称为“千年古会”、“关中第一大集”。腊八会每年“腊月初八”开会,小年腊月二十三结束。占地二三百亩,届时商贾云集、万人聚会、盛况壮观,会场按行业扎设棚帐,自成巷街,纵横交错,坐落有序,南北各货,应有尽有,其中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群马结帮而来,日上市数以千计,为省内最大的牲畜市场。⑥在明清陕西农村,由于交换发达,庙会成为社区行为,往往各村轮流办会,使庙会成为“村村有会,月月有会”的经常性交易行为。
在明清,陕西庙会的繁盛不仅表现在村村有会,而且表现在县县有会,各县的庙会更是盛况空前。可将《陕西通志稿》所记述的各县“赛会”情况摘录如下:
长安、咸宁,“有赛会四,而以四月初八等日都城隍会为最大,商货联集,蔚成巨观”。
兴平,“城内乡人七行逢会之日,行头倡办演戏各费,西南两街均四月,东街三月二十八日,北街二月十二日,外镇如马嵬二月大会七日,店张十二月大会十日,商旅皆来,杂货交易,延展时日”。
高陵,“冬至之会……商贩云集,严如货市,牛马估衣行木各器皆居多数,棚帐互支,经月始散。
泾阳,“鲁桥镇显佑神会,各演戏数日,商贾贩运估衣京货竹器农具木料及牲畜等类,云集贸易”。
富平,“东乡卤泊湖滩以三月十五日商贾云集,百货具备”。
耀州,“二月大会于城东五台山,八月大会于城内南街……商贾云集,杂货畅销”。
镇安,“城隍庙祀神赛会,阖邑奔走,外境商贩亦纷至沓来,扰扰经旬”。
山阳,“浴佛大会,商贾云集,买卖牛马及雨笠锨帚等物,以名农会”。
商县,“有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众,会中多卖农具布疋”。
大荔,“虽以祀神为宗旨而民间借此置买牲畜器具,行之永久,不能废焉”。
韩城,“城隍庙向立有赛会,当道咸承平时,招致外来商贾,极为殷繁……十五以后又移至西乡沟北村,穑事告成,报赛田祖,是时或市牛马,资耕耨或购衣褐,谋卒岁,或抱布贸丝,以有易无”。
华阴,“华狱镇有西狱会,本省京货估衣及外省州县药材各行皆至,搭盖席棚,售买货物并有花马骡马各市约二十余日乃散”。
凤翔,“城隍冬会,演戏数台,狭旬斗聚山积,珍货谷量马牛”。
洛川,“县城三会,粟米交易,县东黄龙山六月九月有会,稍盛,售卖骡马牛羊”。⑦
农村定期集市贸易和庙会的发展,要求打破交换所受到的时间性限制,推动着交换与集镇的常住人口的结合,导致集镇合而为一,产生和发展了比农村集市贸易初级市场更进一步的市镇。在明清的陕西农村,随民间商品流通的兴盛,市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以渭南县明清市镇的消长变化为例:明代嘉靖年间,渭南有市镇16个;到雍正十二年,市镇增加到30个,与明代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到光绪十八年,市镇又增到36个。⑧许多市镇成为著名的农村工商业中心,如户县之秦渡镇,“商贾辐辏,为邑中最盛”⑨,“周围几十里路以内又无大的集镇,每逢集日,商贾云集”⑩;三原陂西镇,“市廛稠密,基砋广袤为邑首镇”(11);朝邑之赵渡镇,“邑名地也,烟户辐辏,被服济楚”(12),“滨渭河,为商贾辐集之所”(13);渭南之孝义镇,“为渭南河北之要区……林木葱茏,人烟稠密,百货聚集其间者,极晦明风雨之无阻,人语喧哗之遥闻,城市之繁庶他属莫能与并”(14);朝邑之赵渡镇,“邑之为市者以十数,而赵渡为最大商贾辐辏,里中一浩穣也,盖称曰市焉”(15);乾县之冯市镇,“为商贾走集之所”(16);甘泉的临直镇,“居民富庶,为县大镇”(17);宜君之百直镇,“为商贾辐辏之所”;保安县之沙家镇,“为商贾往来贸易之地也”(18)。
明代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为人们经商致富提供了人生出彩的舞台。
二、李鸿虞、张忠轩、樊现、张云宵和王舆的经营过程
李鸿虞是泾阳人,他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文人温自知为其撰写的《明故公李鸿虞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鸿虞李翁,幼令丧父,有母尸饔,拘劳万状,赖以成立。翁之事母恪尽孝道,翁习计然之策,遂成良贾,万货之情,亿则屡中,知人而时使之,克勤克俭,居积致富。”成为泾阳“东郭巨族”。(19)
张忠轩是高陵人,他的经营事迹在《张忠轩合葬墓志铭》中有记载:
“处士张公……初业儒……且家贫,菽水不充……遂纯艺黍稷,肇牵牛车,登临巩涉泗水,以图洗腆,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即古之托畎亩鱼盐海市者也。”(20)
樊现是扶风人,他的经营事迹在康海为其撰写的《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樊翁早年丧母,后又为继母所逐,近有破房半间。但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勤俭持家,数年家有中人之产,先走南闯北,以经商成巨富,积赀弥万。”(21)
张云霄是朝邑人,他的经营事迹在渭南文人韩邦奇为其撰写的《张云霄墓志铭》中有记载:
“云霄世为朝邑大庆关人,自祖父来以赀雄于关……张氏毁于盗,赀产几尽……云霄乃舟自刻历,尽反旧好,不数年家至几万金。”(22)
王舆是泾阳人,他的经营事迹在户县文人王九思为其撰写的《明故秦府良医王君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王舆经商发财后,回家买田,“君当此郭买田数亩。创作别业,植花卉竹林。有水有亭,奉其父母居之。比葬母后,日与朋旧高会于此,二子俱成立,又抱孙,而家道甚备,始无意于江湖之迹,其乐陶陶。”(23)
他们五人都是因为经商而脱贫致富,又都因为经商而保持了商人优秀的品质。
李鸿虞是因为习计然之策,靠自己的经营智慧,“万货之情,臆则屡中”,克勤克俭,成为泾阳“东郭巨族”;张忠轩是力农积粟,将农业上的积蓄转化为商业投资,又肯吃苦耐劳,肇牵牛车,经商足迹遍及天南海北,实行农业与商业互相支撑的经营策略,“即古之托畎亩鱼盐海市者也”,取得经营的成功;樊现从破房半间起家,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勤俭持家,从小本经营做起,借他姐姐的嫁妆为资本,走上大规模涉外经营的道路,“走南闯北,以经商成巨富,积赀弥万”;张云霄虽说是商贾之家,但家道几起几落,多亏张云霄“舟自刻历”,逆境奋起,不屈不挠地努力经营,“不数年家至几万金”;王舆是经商发家,然后置田起屋,“其乐陶陶”享受创业成功的乐趣。他们的生活经历证明了“勤奋劳动致富,合法经营发家”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但是,他们发家致富后,并没有奢侈靡费、横行乡里、恃才傲物,而是保持着陕西人节俭内敛的生活作风,保持着优秀商人的品质和修养。李鸿虞是发家后“恪尽孝道”、“克勤克俭”,保持着勤劳动经营作风;张忠轩更是文人下海经商,“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保持着“儒商”的高雅情态;樊现是小本经济起家,发财后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夫妻二人克勤克俭,不忘创业之艰难;张云霄是几经阀阅,经历千辛万苦,才重振家声,因他保持着良好的经营作风,结缘各方,人们认可他的人品,才“尽反旧好”,帮助他渡过难关,梅开二度;王舆是发家后,起华屋孝敬父母,并交结好友,乐施乡邻,才得以尽享晚年的亲情之乐。这些也都说明保持优秀商人的品质、不轻狂张扬、内敛自省、结缘各方是商业经营长兴不衰的社会法则。
同时,他们的成功也说明以贫求富,仅靠吃苦耐劳是不够的。商海无涯,风波骤起,要在充满风险的商海中扬帆远航,还要依靠自身的经营智慧,按照商业经营规律办事,才能获得预期的经营效果。李鸿虞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认真学习商业经营经验,仔细把握商业的供求变化规律,以销定货,趋市供应,做到了“万货之情,臆则屡中”,而且知人善任,设法调动伙计的积极性,才取得了成功;张忠轩更是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商业实践中,用知识指导商业经营,“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保持着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表现了优秀商人的高贵品质;樊现是贩夫贩妇,肖小起家,丈夫走南闯北于外,妻子勤俭持家于内,夫妻共同戮力,才赚得了偌大的家私;张云霄是不畏艰难,“舟自刻历”,满怀逆境不弃的勇气,用自己良好的道德修养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可和周济,才取得了两度创业的成功。这些也都说明在经商致富的道路上,“有力吃力,无力吃智”、“商以察尽财”、“贾以智求富”是商业活动历久不衰的经济法则。
①元稹:《元氏长庆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卷33。
②乾隆:《富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卷2。
③武之望:《广阳镇新市碑记》,见《临潼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④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陕西通志馆本,卷198,《岁时》。
⑤《陕行汇刊》卷8,第2期。
⑥三原县志办:《三原工商行政管理志》,油印本。
⑦均见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陕西通志馆本,卷198,《岁时》,第24-30页。
⑧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第11页。
⑨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2页。
⑩户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户县文史资料》第4辑,第8页。
(11)三原县商业局:《三原县商业志》油印本,第7页。
(12)李天受:《来紫堂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卷1,第25页。
(13)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4页。
(14)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卷10,《艺文志》。
(15)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9页。
(16)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9页。
(17)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7页。
(18)潘锡恩:《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卷229,第8页。
(19)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关中丛书本,卷2。
(20)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87页。
(21)康海:《康对山文集》,关中丛书本,卷38。
(22)韩邦奇:《苑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卷6,第15页。
(23)王九思:《渼陂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