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汉长安
责任者: 武伯纶,武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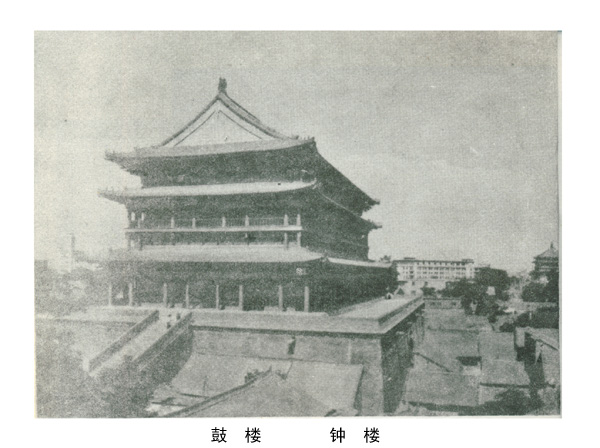

由于秦代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滥用民力,加上秦末战乱的严重破坏,因而汉王朝初期,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物质非常贫乏,以至于皇帝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拉车马,宰相、大将都只得坐牛车①,慢腾腾地颠簸着去上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西汉初期的几个皇帝都采取了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奖励农耕的措施。汉武帝时期更大力兴修水利,使用新式农具,使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由于从函谷关以东各地向京师调拨的工农业产品,主要用船经过黄河西上,再转由渭水运到长安;而渭河河道弯曲,水浅沙多,水量很不稳定,不能经常保持畅通无阻,因此在公元前一二九年,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开凿人工渠道。武帝采纳了郑当时的意见,命令水工徐伯测量以后,动员几万民工,费了三年时间才修成。这就是西起长安昆明池,向东横过灞、浐等河流,直至今潼关县北部流入黄河,全长三百多里的漕渠。漕渠运输比渭河航道缩短了大约三分之二的路程,而且使沿渠两岸一万多顷农田得到了灌溉。这是西汉第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程。
专门为浇灌而修的水渠,除秦代的郑国渠和公元前九十五年(汉武帝太始二年)修的白公渠已经在第一节作过介绍以外,这一时期关中各地还修了六辅、龙首、灵帜、成国等渠道,使大量农田变为水浇地,成倍地提高了产量。
从春秋或者更早时期开始使用的铁器,在汉代已普遍用到农耕上。特别是武帝时期,赵过发明了三脚耧,采用了使土地合理轮休的办法,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脚耧一次播种三行,而且把开沟、下种、覆盖三道工序一次完成,这在当时无疑是农业机械上的重大革命。为推广这种新式农具,汉王朝的大司农专门组织技术高的工匠进行制造,又命令各地的县令、三老、农官和有经验的老农到长安学习操作方法②。成帝时(公元前三二——前七年),氾胜之在农民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了掌握节令气候、辨别土壤特点、御防干旱,以及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的办法,说明西汉时期已经积累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耕作经验。
一九七五年在西安西郊鱼化寨公社,一次就挖出西汉铁制农具八十五件之多,出土地点恰恰位于汉代上林苑故址的范围里。这批农具整齐而又完好地摆在地窖中。近年来,在西安一带的西汉墓葬中,又曾出土大量陶仓、陶廪、陶井、陶灶等,有的上边写着“粟囤”、“麦囤”等字样,仓廪里还往往有残留下来的粮食。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粮食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③由于农业的发展,使长安出现了一派兴旺和繁荣昌盛的局面。《汉书·食货志》里有一段话说:汉武帝初期,除了遇到水、旱灾害,年年百姓富足,城镇农村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的,京城里皇家的钱数百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因而数也数不清。大仓里边的粮食,年年增加,陈粮又加上陈粮,以致腐败得不能再吃。当官的职位很稳定,生活也很优越,连街巷小吏都是美味佳肴大吃大喝。这里反映的,当然主要是皇家贵族和地主阶级的生活情况,但也说明国家的确是富裕起来了,长安的确成了全国的财富中心。这是武帝时期国势强盛、国防巩固、政局比较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西汉的工商业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时的首都长安,最好地反映了工商业的这种繁荣的情况。
手工业中最主要的如冶铁、木工、漆器、制革、丝绸纺织、机械制造、砖瓦业等,较前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拿纺织业作为例子,汉王朝在长安设有东、西织室,集中了大量优秀工人,专门为皇家生产高级丝绸绫绢。民间的纺织业更是竞放异彩,新的技术往往从民间而来。如鉅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人陈宝光的妻子,能织葡萄锦、散花绫等新的花色品种,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便把她召到长安为自己织作。相传陈宝光妻子用的织机有一百二十个镊子,六十天就能织一匹绫绢。
漆器和玉器也是汉代手工业生产的大宗。近年在陕北出土的描花漆盘,在咸阳出土的玉熊、玉鹰、玉马、玉辟邪等,小巧玲珑,造型优美,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有一件民间称为“猴骗马”的玉雕刻品,马上骑着一只猴子,马是正在站起来的姿势,猴子泰然自若地坐在上边,形象生动逼真。
纸是记录文献和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我国是最早发明造纸技术的国家。过去一般都认为,公元一〇五年的东汉时期的宦官蔡伦,是首先造纸的人。但是一九三三年从新疆罗布泊附近的西汉烽火台遗址里,出土了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麻纸,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五月,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出土了包裹铜镜用的纸张残片。铜镜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初期的制品。包裹铜镜的这些纸是由大麻和苧麻纤维制成的,质地粗糙疏松,应该是西汉早期的产品。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张,已被专家定名为“灞桥纸”。事实说明,蔡伦只是在劳动人民长期造纸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一技术,并加以提高和推广的人。
至今还没有发现过完整的汉代机械,但却多次出土过作为机械基本部件的齿轮。一九五六年,在西安附近的洪庆村西汉墓出土了一对人字纹齿轮,制作非常精致。试把两个齿轮套在一块,齿部咬合得非常紧密。这些齿轮原来所在的机械那怕是很原始的,但懂得了运用齿轮传力,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创造。文献记载:长安巧匠丁缓能制造七轮扇,由一个人运转这种带有七个轮子的大扇,使满屋凉爽非常④。这也是当时利用齿轮传力的一个证明。
前边说过,建筑业在汉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西安地区今天虽然已经看不到西汉时代完整的建筑物。但在遗址地区却可以看到许多作为建筑物重要构件的砖和瓦。汉砖有长方形、方形和空心的多种类型。砖的正面大都有装饰图案,如狩猎纹、几何纹图案。少数砖上有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四神图”的浮雕。
带瓦当的瓦是装在建筑物椽头上,专门用来保护木椽的。战国时期建筑房屋已开始使用瓦当,汉代更加盛行起来。西汉瓦当面上大都有突出的阳纹图案或者文字。这些篆书或者隶书的文字,刚劲有力,布局匀称,象是一枚放大了的古代印章。一个好的瓦当,就是一个好的艺术品。
瓦文的内容,有标记官署名称的,如“石渠千秋”、“都司空瓦”、“上林农官”;有称颂胜利的,如“汉并天下”、“大汉万世”、“乐哉破胡”;有表示吉祥的,如“长乐未央”、“安乐富贵”、“延年”;有陵墓专用的,如“长陵四神”、“冢上大当”等。因为很多瓦当标明着官署、宫殿或者陵墓的名称,是各类建筑物的专用品,因而往往可以从它出土的地点判断这些建筑物的所在地。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给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商品,造成了城市的繁荣,这一点以长安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长安城里有九个集中的市场,西部六个,东部三个。每个市场都有围墙;市场中修建了高达五层的市楼,名叫旗亭,从这里可以看到各个街道上的情况。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当日长安商业贸易的盛况说:九个市场开业,琳琅满目的商品分类排列,热闹拥挤,人难得转身,车不能掉头。城里塞得满满的,旁边还有很多买卖。街道上烟尘四起,上接云天。由于有这么兴旺的市场交易,因而在古代文献里记载,即便一些卖浆、贩脂、出售肉干和磨刀剪的小商贩,也都发财致富了。
至于谈到西汉时期学术文化的光辉成就,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长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如前所述,萧何跟随刘邦初进关中时,把秦丞相府的书籍收藏了起来。汉初的几个皇帝,也都非常重视收集和整理图书,惠帝时特别解除了秦代规定不准民间藏书的禁令。后来刘向等人把这些书籍加以整理,共得一万三千二百余卷。司马迁以这些书籍为参考,写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记传体通史。它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几种不同的体例,反映了上起黄帝,下到汉武帝,长达数千年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过程。司马迁用词准确,语言生动,尤其善于用简练的笔墨,表现出性格不同、面貌各异的人物形象来,往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史记》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西汉末年刘歆继承他父亲刘向的遗业,把汉皇家藏书加以校勘、分类、编目后写成定本。目录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个部分,统称《七略》。《七略》不仅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先导,也是一部宝贵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可惜原书已经散佚,仅能从后人辑本中看到其中的部分内容。
汉初教育事业还不发达,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开始只有五十个学生。到武帝末年,学生增加到三千人,并且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全国各地都选送青年到长安留学,推动了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相传蜀郡太守文翁送十几名学生留学长安后,就使蜀地的文化提高了一大步⑤。
当然任何历史时代,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西汉国家政权和以后各朝代的国家政权一样,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因而特别推崇能反映地主阶级要求的儒家学说。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借利禄官爵鼓励人们钻研儒家经典。所以当时虽然学术界有许多流派,都不过是儒家的分支罢了。许多人在研究中繁琐考证,盲目崇拜,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⑥,形成了很坏的学风。
由于封建社会本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各种矛盾,因而在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国都长安城中,统治阶级内部也形成一股起破坏作用的势力,这就是一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富豪与官僚贵族勾结起来,肆意妄为,造成混乱和灾难。例如《汉书·货殖传》中说的:从汉元帝到王莽时期,长安城里的樊嘉、挚网、如氏、苴氏,以及卖丹药的王君房和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等人,都是能呼风唤雨的大富豪。王孙大卿能“以财养士,与雄杰交”,被王莽委任当了管理长安东市的令长。
这些人唯利是图,活动能力都很大,对于妨害他们“谋取暴利”的那怕是显宦贵官,也极力设法给以报复。宣帝时期,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富豪焦氏、贾氏,屯积了大量丧葬物资,准备在皇家贵族急用时索取高价。阳城侯、大司农田延年,奏请皇帝批准后,没收了这些物资。因而焦氏、贾氏等人怀恨在心,他们不惜花大钱寻求田延年的过错。田延年终于由于这些人告发他有贪污罪,而被迫自杀⑦。
豪家富户又经常在朝官们的支持下欺压市民。长安一个叫萭章字子夏的人,住在城西柳市,号称“城西子夏”。他因为与中书令石显交结,因而门前车马不绝。历史记载说:城西的萭章、东市的贾万,及卖剪刀的张禁、卖酒的赵放和杜陵(位于今陕西省长安县)杨章等人,都是长安城中的“宿豪大猾”。他们无不“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而且对这几个为非作歹的家伙,一连换了几任京兆尹也没有办法⑧。这正说明他们是有大靠山的。
汉武帝时期,一些贵族子弟和街巷恶少,更借替人报仇,收受贿赂和抢劫财物。他们在袋中装上不同颜色的弹丸,规定凡摸得红丸的杀武吏,凡摸得黑丸的杀文官,凡摸得白丸的,负责办同党有被别人杀死后的丧事。因而当时长安城中,经常出现“剽劫行者,死伤横道”的阴森凄惨的场面⑨。
①见《汉书·食货志》上。
②见《汉书·食货志》上。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四卷本,第四卷,第一四五页。
④见《西京杂记》第一卷。
⑤见《汉书·循吏传》。
⑥《汉书·儒林传赞》。
⑦见《汉书·田延年传》。
⑧见《汉书·王尊传》。
⑨《汉书·尹赏传》。
出处:西安史话/武伯纶,武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