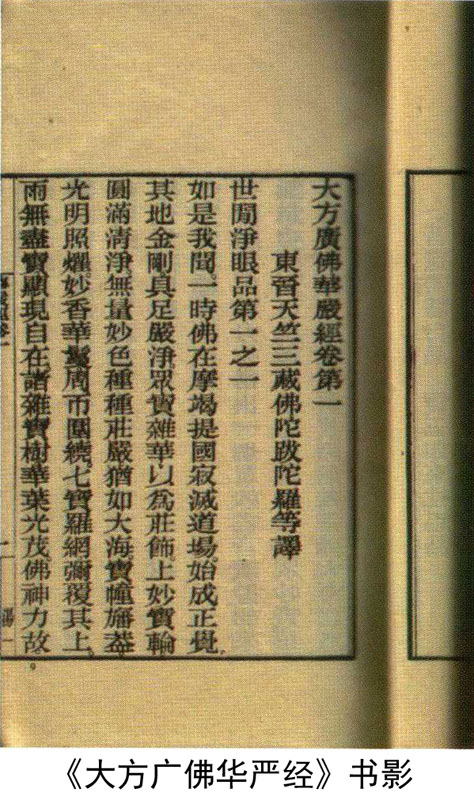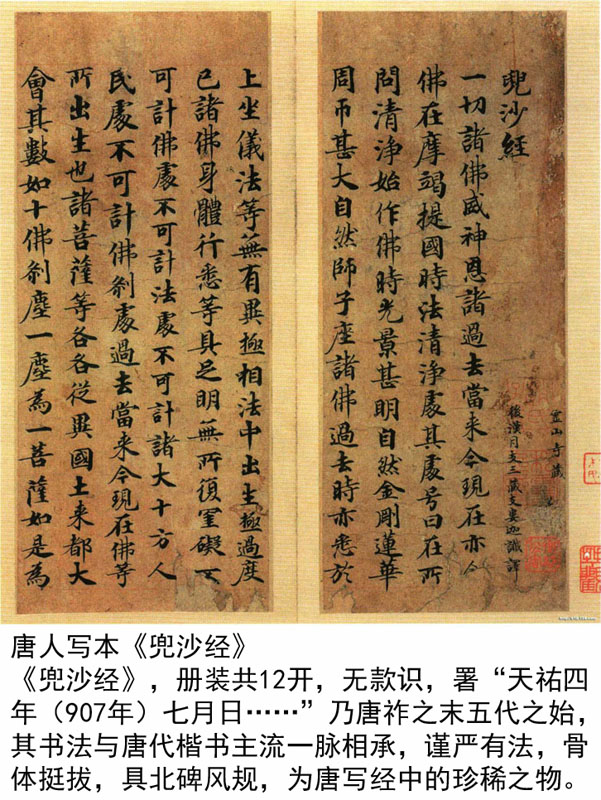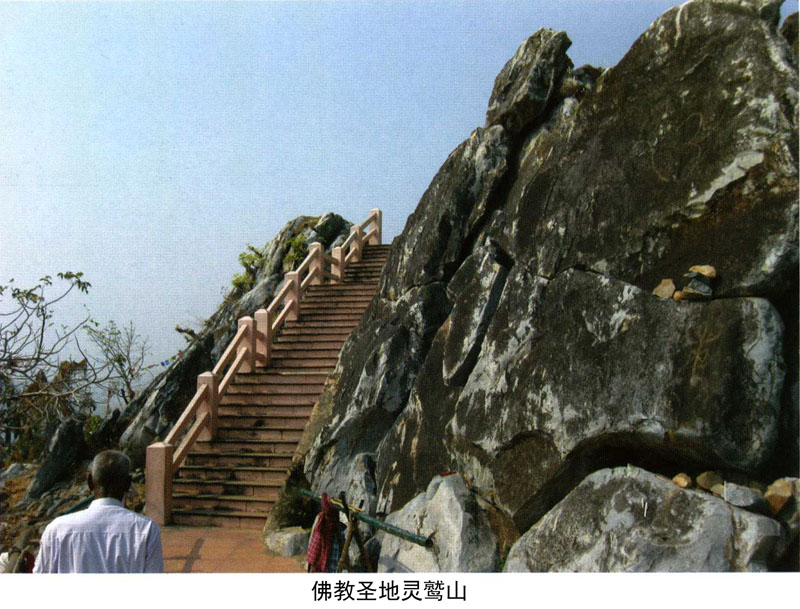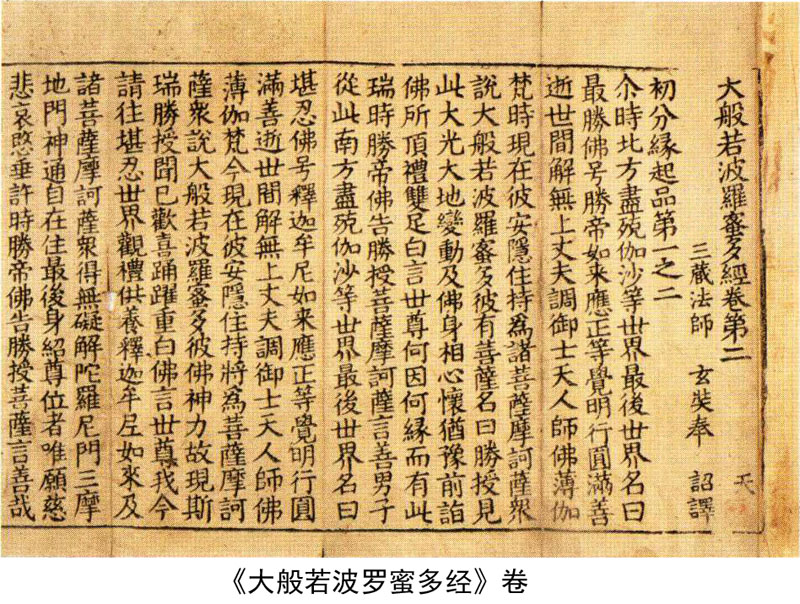从现有资料可知,佛教典籍最初大抵均为偈颂。这是因为偈颂便于记忆,与佛教早期口口相传的教授方式相适应。
偈颂往往比较简略,难以容纳比较丰富的内容与深奥的义理,所以还是需要有叙述性或论说性的散文。后来,佛典中的偈颂与散文往往配合起来,错落组合,从而形成佛教典籍特有的文体。在这种文体中,散文一般称为“长行”。再往后,便出现完全由散文组成的经典。
一般来说,早期佛典的一首偈颂或一篇偈颂、长行错落组合的文字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论述。篇幅也都不长。如现在保存在《法句经》中的偈颂与保存在《杂阿含经》中的1362个篇幅短小的经典就反映了早期佛典的若干特征。由于经典的篇幅短小,内容繁杂,数量又多,这就给记忆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佛典逐渐以类相从进行组织。现知较早的佛典组织形式是“九分教”。
九分教,又称“九部经”、“九部法”。据《法华经·方便品》的说法,它们是:
(一)修多罗,意为“经”、“契经”、“法本”。一般是指主要用散文形式组织成的经文,也包括偈颂、散文错落组合的经典。
(二)伽陀,意为“讽颂”、“孤起颂”、“不重颂”。一般是指用偈颂形式组织成的经文。
(三)伊帝日多伽,意为“如是语”、“本事”。指释迦牟尼说的弟子们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四)阇陀伽,意为“本生”或“生”。内容俱系释迦牟尼说的自己在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五)阿浮陀达磨,意为“未曾有”、“希有法”。内容主要是叙述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种种神通变化故事。
(六)尼陀那,意为“因缘”、“缘起”。记述释迦牟尼说法的原因。
(七)阿波陀那,意为“譬喻”、“解语”。指设用各种譬喻来宣说佛教教义。
(八)耆夜,意为“应颂”、“重颂”。指用偈颂的形式将散文中宣示的教义再提纲挈领地复诵一遍。
(九)优波提舍,意为“论议”。是探讨诸法意义的经文。
九分教中的修多罗、伽陀、耆夜三类是按照佛典的基本体裁所创立的名称;阿波陀那是依据论述方法而创立的名称,其余五种则是依据经文的内容所创立的名称。立名的标准既不统一,则进行实际的分类操作时想必会有一定的难度。由此可知,九分教是对佛教经典进行分类的初步尝试,分类体系与方法远还没有成熟。我认为,九分教所以成为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形式,想必有自己的一段形成历史。亦即它不是在某次对佛典进行全面整理时产生,而是将前人的分类整理成果,分阶段予以积累的结果。
从佛教史的角度,以事物的出现必然由小到大、循序渐进的观点来说,所谓第一结集时就已经会诵出全部经藏、律藏的说法,恐怕不一定可靠。而上述九分教的形态则相对比较古拙。九分教中提到的各类经典,现不少在南传巴利语三藏及汉文大藏经中均可看到,由此证明印度的佛经当时的确曾有过这么一个发展阶段。因此,虽说我们并不能肯定九分教这种形式产生于第一结集,但可以认为它是我们现知的关于印度佛教典籍的最早组织形式。
《法华经·方便品》主张上述九分教是小乘经典的组织形式。那么,小乘的早期佛典是否完全按照《法华经·方便品》所说的那九种分类组织呢?这还是一个疑问。因为不少经典都提到九分教,内容却各有参差。像《大集法门经》、《十住毗婆沙论》等,对小乘九分教的说法与《法华经》不同。又如《大般涅槃经》认为小乘没有“无问自说”,在《法华经》的上述小乘九分教中的确也没有“无问自说”,但在现存的小乘藏经——南传巴利三藏中却偏偏存在着“无问自说”。因此,小乘九分教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小乘的九分教大约因部派的不同而相互有异,本身并不统一。也就是说,九分教的出现与小乘部派的出现大体同时。由于当时九分教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规范。所以,虽然有若干小乘部派接受这种分类法,但由于大家对这种分类法的理解不同,操作的结果自然也各不相同。
继九分教之后出现的佛藏组织形式是“十二品经”。十二品经又称“十二部经”、“十二分教”、“十二分圣教”等。它是在上述九分教的基础上加上:
(十)和伽罗那,意为“授记”、“授决”。系释迦牟尼预言小乘弟子将来生死因果及预言大乘菩萨将来成佛的记述。
(十一)优陀那,意为“自说”、“无问自说”。指无人发问,释迦牟尼主动宣示的那些教义。
(十二)毗佛略,意为“方等”、“方广”。指释迦牟尼所说的广大平正,比较深奥的教义。
比较九分教与十二品经,可知十二品经是在九分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印度佛教从小乘向大乘演化时期的佛典组织形式。
后来,《大般涅槃经》又有“大乘九分教”的说法。所谓“大乘九分教”系从十二品经中删去因缘、比喻、议论三类后,由下余的经、讽颂、如是语、本生、未曾有、应颂、授记、无问自说、方广等九类组成。隋慧远在《大般涅槃经义记》卷二中解释了小乘、大乘九分教的区别。他说:对小乘教徒来说,他们并不要求成佛,所以不用授记;当时释迦牟尼所说的法比较浅显,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所以释迦牟尼用不着“无问自说”;当时还没有宣说那些深奥的教义,自然也就没有“方广”。而大乘教徒都是一些有悟性、有根机的人,根本用不着凭借“因缘”、“比喻”、“议论”之类的方法,很快就能领悟佛法。慧远的解说,反映了大乘教徒对此的态度。所以,《大般涅槃经》所谓的大乘九分教,只是借用小乘九分教的形式对十二品经进行改造,为自己服务罢了。
十二品经及大乘九分教产生于小乘向大乘演化时期。所以,其中既包括小乘经典,也包括大乘经典。那么哪几类属于小乘?哪几类属于大乘呢?不同佛经的说法也有不同,甚至同一部经先后说法也不一样。如《大般涅槃经》卷三,说大乘九分教中九类经都属大乘;而卷五,又说只有“授记”、“自问”、“方广”三类属于大乘。另外,《菩萨地持经》说十二品经中,只有“方广”类典籍属于大乘,其他十一类经典都算小乘。这些不同的说法反映了不同的佛教派别对佛教典籍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这些典籍或分类法与各佛教部派的关系。
上述九分教与十二品经是否包容了当时社会流传的所有佛教典籍,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初期佛教与部派佛教都十分重视教团的戒律生活,当时,各种各样的关于戒律的佛典已经被编纂出来。然而,在上述九分教与十二品经中,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些律典的位置,这说明当时的律典被置于九分教与十二品经之外,说明九分教与十二品经实际只是佛教对后代三藏中被称作“经藏”的那部分典籍所用的分类法。
总的来说,九分教与十二品经是印度佛教对典籍进行早期整理时的分类法。这种方法很可能只在某些地区或某些部派、某些典籍范围内使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也没有在整个印度佛教中流传开来。后来随着三藏的形成,这种分类法逐渐被废除,仅在某些典籍中留下它的名称。
十二品经所述的这些经典虽然没有完全传入中国,但这一名称却在中国广泛流传。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把“十二品经”一词当作大藏经的代名词来使用。比如南北朝梁代著名僧人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说:“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后说。契经以诱小学,方典以劝大心。妙轮区别,十二惟部。法聚总要,八万其门。”就把“十二部经”当作全部佛典的代表。有些典籍认为,只念诵十二品经的名称也可以有无量的功德,敦煌遗书中就存有专门抄写十二品经名称以供念诵的写卷。南北朝时,中国出现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佛名经》,专门念诵供奉佛、法、僧三宝的名号。其中作为法宝的代表就是各种佛经,《大佛名经》在念诵这些佛经时,前面都要念上一句:“次礼十二部经大藏法轮”,表示虽然只念诵某些经名,但供养的是全部佛教大藏经。隋代静琬发愿在房山云居寺刊刻石经,最初拟刻十二部经。为什么只刻十二部经呢?那是因为静琬自觉有生之年未必能够把全部藏经都刻在石碑上。所以决定只刻十二部,借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刊刻全部佛经的心愿。后代文人的文集中也常常用“十二部经”来代表整部大藏经。但后人不理解它的意思,往往搞错。如《白居易集》中好几处都出现这一名词,但点校者不察,给它打上书名号,成为“《十二部经》”。把它当作一部名叫“十二部经”的经典了。
后来,印度又出现用经、律、论三藏来组织佛教典籍的分类法。那么,经律论三藏与十二品经的关系如何呢?这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比如《瑜伽师地论》认为:契经、应颂、授记、讽颂、自说、譬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等十类典籍属于经藏;因缘属于律藏;论议属于论藏。而《大乘阿毗达磨集论》认为:契经、应颂、授记、讽颂、自说这五类属于小乘经藏;方广、未曾有这两类属大乘经藏;缘起、譬喻、本事、本生等四类属大、小乘律藏;论议则包括了大、小乘论藏。由于当时印度的典籍基本上已不再采用十二品经这样的分类法,所以各派的这些观点只表示了他们对佛典分类历史的一种追述,对于现实的佛典的分类已不起多大的作用。等到“杂藏”这一概念出现后,《四分律》还主张十二品经统统都属于杂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