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产生及发展——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作者:刘进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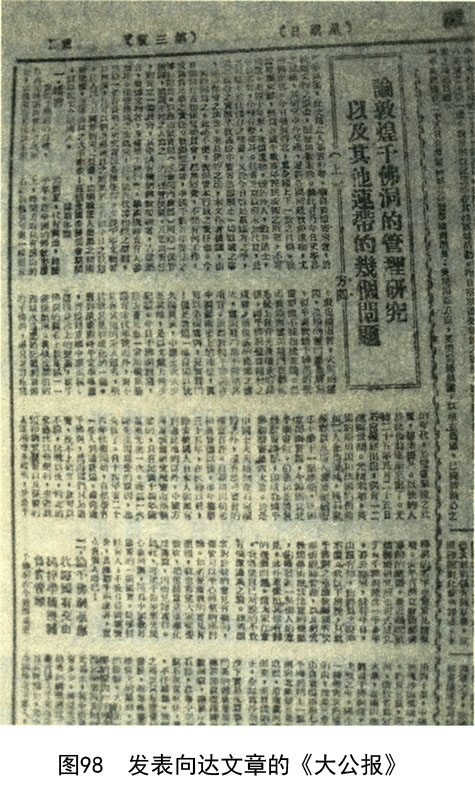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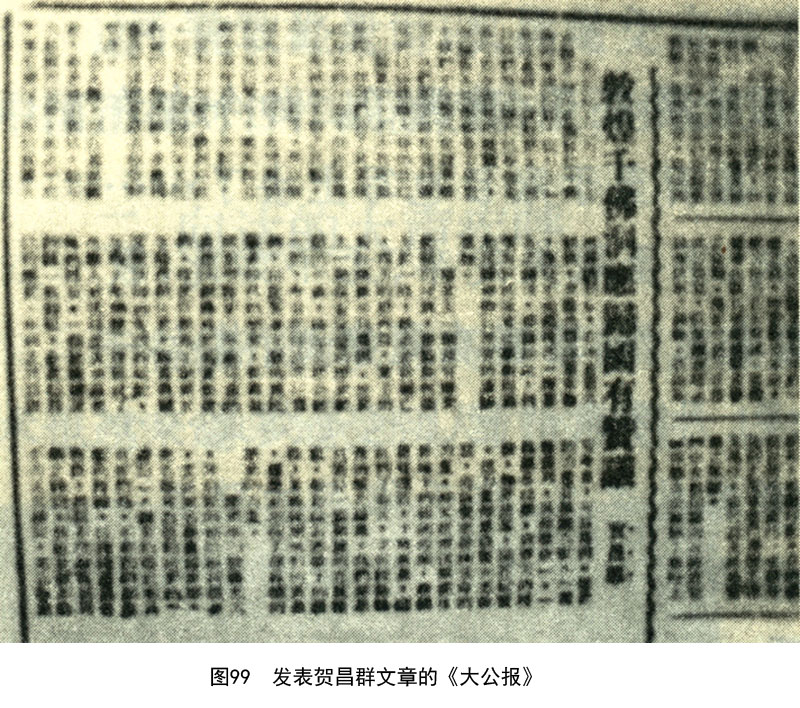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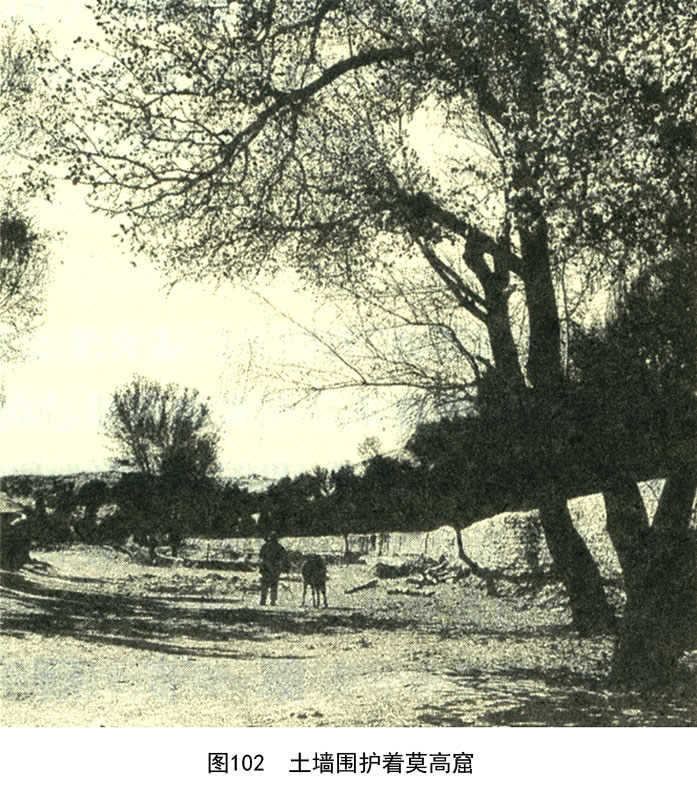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同时,历经磨难的敦煌石窟艺术也才得到了保护、临摹和研究。那么,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怎样成立的呢?
一、于右任的建议书
提起敦煌艺术研究所,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于右任。1941年甘新公路正式通车,时年63岁的于右任即由重庆来西北考察。10月2日抵西安,旋过兰州,趋敦煌。10月5日,恰值中秋节到了莫高窟。这时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在洞窟临摹壁画,当晚即在张大千的临时住所过中秋节,同到者有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曹汉章、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张公亮、任子宜、李祥麟、王会文等。席间,大家的话题自然谈到敦煌和敦煌艺术,认为敦煌文物多年来不断遭到外人的劫夺,目前大量艺术珍品得不到妥善管理保护,许多洞窟濒于坍塌;由于气候恶劣,有的壁画大块脱落,而有关方面却对敦煌国宝漠然视之。在座诸人无不痛惜。在以后几天的参观考察中,对敦煌艺术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它濒临毁灭的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敦煌纪事诗》①曰: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敦煌之行结束后,又考察了河西走廊,复到兰州、西宁。1941年12月11日,完成了对西北的考察。14日离开西安,返回重庆。在兰州时,曾谓莫高窟是中国的骄傲,更是甘肃的骄傲,应珍视!在他考察敦煌后,深感现状岌岌可危。因此返回重庆后,就立即在政界、学术界大声呼吁,希望重视、保护敦煌艺术宝藏。作为政府高级官员,亲自撰写《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并送达国民党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这一建议书发表于当时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2卷4期(1942年2月15日出版)②,建议书说: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岩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保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骗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灭。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画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这个建议经过讨论,决定交当时的教育部负责筹办。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在对日作战激烈阶段,财政支出紧张,故答复须待次年始能成立。
二、向达的大声疾呼
于右任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其建议在当时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敦煌艺术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1942年5月,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件,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就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1942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应研究院之约,参加历史考古组赴敦煌等地考察。通过考察,更认识到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价值,看到了千佛洞所经历的劫难及其被毁灭的危险,立即在莫高窟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以“方回”为笔名,在重庆《大公报》1942年12月27~30日发表。向达在文中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政府重视祖国文化遗产,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保护敦煌文物。向达指出,敦煌石窟遭受毁坏的原因,大概可分作自然的与人为的两个方面。
说到千佛洞受人为的原因所摧毁的话,就复杂了……每年到阴历四月初八日,敦煌人几乎倾城的来到千佛洞礼佛。千余年来这些善男信女到千佛洞来礼拜烧香,每一个人只要在壁画上轻轻摩一下,壁画就算是铁铸的,也会磨穿了。如今千佛洞壁画上供养人像和供养人题名之所以十九漫漶,不能辨识,原因大半是由于礼佛的人,挨挨挤挤摩摩擦擦所致。还有千佛洞离城四十里,中隔戈壁,礼佛的人,不能当天来回,势非在此住夜不可。千佛洞现有上、中、下三寺(下寺是盗经的王道士所新修的,原无下寺之名)。房屋不够住。和尚道士为省事方便起见,便在一些比较大的窟里或窟外,筑起炕床,打起炉灶,以供礼佛的人过夜烧饭之用。这一来壁画自然毁了。礼佛本来是一种功德,如今反而成为罪恶,这真是始意所不及料的!千佛洞壁画有一部分毁坏成为黑漆一团,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民初将白俄收容在千佛洞里,于是凿壁穿洞,以便埋锅造饭出烟,好多唐代的壁画都因此弄坏了,熏黑了。如今在许多窟里,壁上还有当时白俄的题壁,漫画,甚而至于账目也写上去了……此外中国人喜欢到处留名,上自学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如此,敦煌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敦煌人于普通题名之外,还喜欢题字谜,甚么一字破四字破的字谜,千佛洞随处可以看见,月牙泉的壁上也是如此……至于有些人士如华尔纳之流,藉着研究考察的名义,将千佛洞的壁画一幅一方的粘去或剥离,以致大好的千佛洞弄得疮痏满目,这种盗窃和破坏古物,律有明文,国有常刑,自不在话下。
……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我这一个建议,特别注重纯粹学术机关六个字,所以表示千佛洞的管理与玩古董讲收藏不同,这是要用近代博物馆的方法与用意去管理的。还有一点,就是纯粹学术机关不受政治上易长的影响,主持者既不至于五日京兆,也可以免去因常常交代而生出的一些毛病。
……
千佛洞收归国有,国家免不了要花上几十万作初步的修理和保护工作;设立管理所和办事处,国家也免不了一年花上十万或八万的经常费。在目前“司农仰屋,罢掘俱穷”的时候,岂能把有用之钱,花在这些不急之务上面,但是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图存,为的是甚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吗?
向达作为著名学者,他的呼吁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与响应。有的学者就是看到了他的呼吁后,才知道了敦煌宝藏,才下决心去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如潘絜兹读了向达的文章后说,它“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怦然心动了。……下决心要到敦煌去,哪怕只看上一眼,死也瞑目。”③从而历经艰险到了敦煌,加入了敦煌艺术研究的行列。
三、贺昌群的积极响应
贺昌群先生是著名敦煌学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形成了一股敦煌热,而在我国却注意者寥寥。为此,贺昌群先生大声呼吁国人重视敦煌学,他说:“我们只要在这中间抓住一鳞片爪,也可以牵引起许多新问题。至于敦煌石室中所发见的古文书以及多种语言的手写经卷的研究,那真是沃野千里,只待人开拓,西洋的东方学者以及日本人,现在已经去得远了,我国学术界目前似尚无暇及此!”④他不仅对民族文化事业忧心忡忡,并且身体力行,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等敦煌学论文,还翻译了斯坦因的《敦煌取经记》。1942年12月,向达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有关莫高窟的文章时,贺昌群正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他随即在《大公报》1943年1月7日发表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一文作为响应,指出:“历史上一个没有历史记载的民族,无论如何强大于一时,终必至于灭亡”,“一个不知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未有能昌盛的。”从历史的高度,强烈呼吁国家拨款和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敦煌千佛洞。
贺昌群在文中说:
我们十分赞成他(向达)这番建议,我们希望政府也同样尊重这个建议。他的话已经言尽意至,本不用再加申说,但我们为了更当促起政府的注意,知此事为千百年国家文物之所系,非一二人之私言,所以愿借报章的地位,希望舆论界亦加以赞成,使其能比较普遍地为国人所了解,不单对于敦煌千佛洞如此,便是别的有关国家文化学术的古物遗迹,亦应同样具有这种意义去保存和管理。
……
保存古物的机关,我们本有古物保管委员会,不过该会原只保管古物,遗迹之保管不在其职责之内,加之经费拮据,人才零落,恐难负推广之责。傅孟真先生建议应由教育部会同内政部设立一保管机关如委员会之类。我们以为若此委员会之职责能包括管理全国规模较大或价值最高的遗迹,如千佛洞,云岗,龙门以及房山石经寺,嘉祥武梁祠,大同与蓟县的辽金建筑等,那么,傅先生的建议我们极端赞成,但在抗战期中,此事必难实现。若单为敦煌千佛洞而由政府组织一委员会,则政府在百忙中,未必能迅速办到,而目前千佛洞壁画之遭劫,已迫不及待,照方回先生、在千佛洞目睹情形看来,一年四季的游览者和那班学画的人,正在进行剥离壁画的工作,“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真是何等痛心的事。在政府未决定统一管理之前,我们以为目下对于敦煌千佛洞的当务之急,应由政府(教育部会同内政部)迅速指定纯粹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馆负保管之责,保管费当另由政府酌拨。此事之实现愈早,千佛洞之劫运或犹可挽救于万一。总之,千佛洞的应归国家管理,当已不成问题,我们万分希望政府与社会人士早日促其实现,岂仅是学术界之幸而已。
四、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影响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敦煌学史上重大事件。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议,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目前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于右任1942年2月15日的“提议”,作为国民政府大员的于石任,对于在敦煌设立研究机关显然胸有成竹。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1月18日,距于右任发表“提议”不到一年,可以说,最后决策此事和于右任有直接关系。当时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不是常书鸿,而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于右任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这也可以说明于右任的影响。当时发表的名单中,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是委员,1943年3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张大千和王子云都没有出席,也没有参加研究所以后的活动。王子云对常书鸿任职只有一句评价,即“常一直是画西洋油画的专业者”,言下之意,对雕塑艺术还是外行,由他“来筹备这样的工作似乎没有道理的”⑤。
或曰,在于右任“提议”之前,教育部对敦煌的考察和机构设置已经在筹划进行之中。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早在1940年8月就成立,当时决定此事的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和社会教育司长陈礼江,而为王子云递呈报告的是王子云当年的师范学校同学徐朗秋,其时正在社会教育司做科员,官不大,但是很能办事,以后做了西北大学教务长。他在1955年的“交代”里说:王子云和当时教育部上层无一人相识,被任命为考察团团长,就是因为陈立夫和陈礼江“口袋里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考察团成立之初,敦煌就是最重要的目标,而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内地考察,也等于是为敦煌考察练兵,提出成立研究机构的建议,正在考察团分内。虽然现在找不到王子云“建议”的文字,但他从事此项工作之初,便招收的是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其工作方式,与于右任“建议”所云“招收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本趋一致。显然,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考虑,考察团成立之初,便为题中之义。
关于研究所的成立,据王子云回忆:“我们考察团于1940年到敦煌后不久,即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列出具体计划。建议书寄到重庆,恰在此时,重庆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一些因抗战流亡的艺术界人士,特设立一个闲散机构——艺术教育委员会,油画家常书鸿在这个委员会当秘书。我们的建议当然先送艺术教育委员会,于是不仅批准,而且常自告奋勇,愿意远去边塞,筹备研究所的成立,并印出一个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是主任筹备委员,把我列为副主任委员。”⑥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没有参加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五、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正是由于政界、学术界于右任、向达、贺昌群诸先生的诚恳建议和大声疾呼,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与赞成,国民党政府始决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2年春,于右任的建议送达政府研究后,决定次年成立研究所。1942年秋,即开始了筹划事宜,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找到常书鸿,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后来监察院参事陈凌云也对常书鸿说:“于右任建议教育部准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想让你去当筹委会副主任。筹委会主任由陕甘宁监察使的人担任。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回去报告。”⑦常书鸿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始筹划研究所的成立工作。
开始筹划时,常书鸿要让教育部指派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同志,但教育部负责人回答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到当地(兰州)去解决。”这样,常书鸿便只身从重庆珊瑚霸机场乘飞机来到了西北古城——兰州。
常书鸿到兰州后,首先拜访负责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官员们。“开始,这些当地的绅士名流对我还算热情,他们齐声赞许我不辞辛苦,前来从事敦煌艺术的研究保护工作。后来有人提出把所址设在兰州的意见,我说:‘设在兰州,远离敦煌二三千里,还搞什么研究和保护工作呢?’这一来,他们嘻笑的脸上立即挂上了一层冰霜。结果,对于我提出的工作要求,如配备绘画、考古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购置图书参考资料、绘画物品和摄影器材等一个也没有解决。”⑧
常书鸿一人毫无办法,一天天在兰州消磨时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见了一位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学生龚祥礼。他俩一见如故,龚祥礼欣然应允随同常书鸿前往敦煌,并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凑了一个文书,还指派了天水师范学校的校长李赞庭为秘书。最后又在省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中招聘了一位名叫辛普德的会计。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一行六人,乘着一辆敞篷卡车,开始了敦煌之行。经过一个月的艰难旅行,于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3月24日,终于到达目的地——敦煌。这时教育部正式宣布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高一涵、常书鸿、郑通和、窦景椿等组成,任命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常书鸿为副主任。经过筹委会委员近一年的奔走张罗,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2月1日正式成立,直属教育部,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并从重庆征聘来了20余位自愿到敦煌的专业人员,开始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临摹和研究。
① 杨中州选注:《于右任诗词选》,249页、25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② 许有成编著:《于右任传》,190~19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屈新儒:《关西儒魂;于右任别传》,329~3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③ 潘絜兹:《敦煌的回忆》,载《文汇增刊》,1980(6)。
④ 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原载《东方杂志》28卷17号,1931。此据《贺昌群文集》第一卷,200~201页,商务印书馆,2003。
⑤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71页,岳麓书社,2005。
⑥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71页,岳麓书杜,2005。
⑦ 常书鸿:《铁马响叮当》,载《文化史料丛刊》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⑧ 常书鸿:《铁马响叮当》,载《文化史料丛刊》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丝绸之路敦煌研究/刘进宝著.—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