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秦国靠边地贸易发家的红顶商人——乌氏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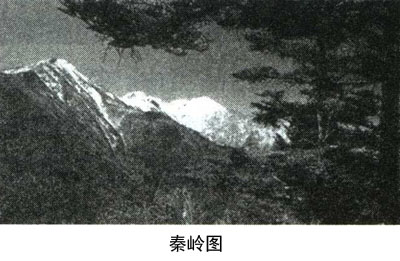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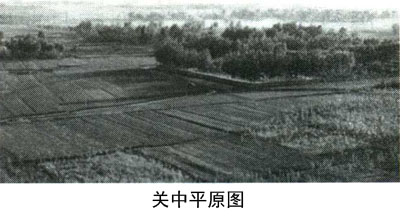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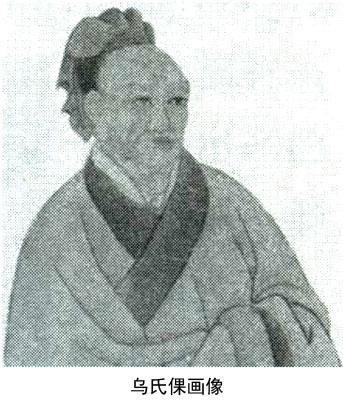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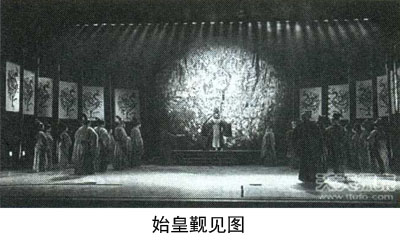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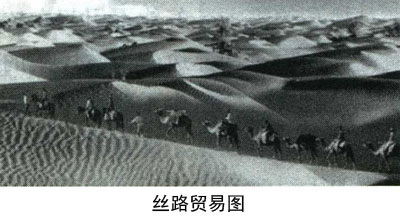
乌氏倮、寡妇清,
封君筑台,礼抗千乘,
牧长穷山,惟商显荣,
嗟我耕战,萤萤其功,
耕者功,战者功,
商者独萤萤。
有国法,有王命,
解我年馑者何无功。
这首秦国当时流传的民谣,说明秦汉时期陕西处于中国农耕经济与西部畜牧经济交换的顶端,两种经济结构各自产品的单一性使这一地区成为交换性最强的地区。利用这一区域优势,乌氏倮“牧长穷山,惟商显荣”,在经营边地贸易中“封君筑台,礼抗千乘”,成为秦代受秦始皇册封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一、秦汉西北的边地贸易
华夏民族最初是以黄河流域为活动范围,而这些地方整个是黄土地带,广袤而又肥沃的土地,使人们得以从事农业生产。黄土地带虽不适于森林的滋植,但宜于作牧地,黄土地上滋生细草,宜于畜类的繁殖。不过中国古代的畜牧还不是很发达,大约到西周末年,牲畜在农业经济当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春秋时代,所谓中原一带还是华夷杂居,以农耕为主,农业在黄河流域已很普遍。当时的中国,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北方包括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以及河西一带地方,属于畜牧经济区;江淮以南秦岭区域和陇西,都算是森林经济区;中间以“三河”为中心连同关中以及蜀和广汉两郡一带地方,构成精耕农业经济区;这三个区域,代表着三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三者的互相竞斗,充满了春秋战国,尤其是秦汉帝国时代的历史。
秦汉帝国内部的物产分布,受三大经济区域板块的影响,各自都有极强的产品单一性。西北一带所出产的主要是畜牧产品,如马畜、皮革、筋角、旃裘之类,所以说“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而中原农业经济区,对马匹和裘革极感需要。反之,畜牧民族所希冀中原的除了酿酒用的蘖秫、谷米之外,对中原的丝织品具有极大的需求,为了获得这些他们生产不了的产品,畜牧民族常常兴兵劫掠。双方这种经济上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所以西北边界的滋扰始终不得休止。汉帝国的后半期,终于演成畜牧民族的大侵入,倾覆了汉帝国。
中原农业经济区域的出产,主要是农产品,除此外值得称道的就是淮河上游漆和齐鲁一带的蚕桑。关于古代汝颍一带产漆,据《禹贡》,豫州和兖州的贡品当中,都有漆。《周礼·职方》讲豫州的出产,也提到漆。《货殖列传》列举可以与千户侯相等的财产时,也特别举出“陈夏千亩漆”。可知在那时候,这一带地方是漆的主要产地。太史公所说,有漆千斗,可比千乘之家,可见漆是当时大宗出产和中原的一大富源。而其间最具重要性的要数蚕桑。蚕桑到秦汉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主要经营蚕桑业的,要算是土宜桑麻的齐鲁卫梁宋一带,①而以临淄和襄邑为中心。《左传》晋公子重耳将去齐,谋于桑下,蚕妾闻之,似乎当时齐国上下,都习于此业。丝织品的消费者主要是当时少数的贵族。孟子说:“五十者可以衣帛”,还是一种奢望。《盐铁论》上说:“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知古代一般平民的衣料乃是麻布。丝织品的销路,当时主要是西方的夷狄诸国,不仅贵族本身,连他们的奴婢也都穿着锦帛绫罗。所以,秦汉之际,岁赐匈奴和历次出使所携,都是以丝织品为主。另外,当时的经济生活,大体是家庭自给自足,平民自己所需的麻布全归自家织作,只是偶然出现于市场。反之,丝织品的生产者,除了官府特别所需外,完全是为市场生产,因此,丝织品成为当时的另一大宗主要商品。后来随着汉帝国的势力和声威,这种制造品沿“丝路”一直销到西域诸国,最远到了罗马。
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当时蚕桑与皮革之间的交换,成为西北边地贸易的主要内容,将中原的丝绸贩运到边地,再将边地的皮革贩运到中原,在丝绸与皮革的对流中,赚取大量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是最能发财致富的经营项目。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正确指出:“孝文、德、缪居雍(今凤翔),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株邑(今临潼),栋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②,说陕西是出大商人的地方。而移民到边地的乌氏倮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秦商的一般面貌。
二、乌氏倮的经营概况
《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乌氏倮的经营状况有所记载: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③
据此可知,乌氏倮是乌氏(或“兀者”)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乌氏最初是中原族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相传少昊作东夷部族首领时,以鸟名任命职官,有“乌鸟”一职,其族徽为大乌,族中有姓氏为“乌鸟氏”者,专职负责掌管高山丘陵。春秋战国时期,朝廷迁徙中原人民实边,乌鸟族逐渐西移,陇西地区有乌氏国(今宁夏六盘山),是西戎民族义渠戎部族的一个分支。乌氏国被秦国攻灭后,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在乌氏戎族的主要居牧地设立乌氏县(今固原南部与甘肃平凉北部一带),其国人中有以故国名为姓氏者,就称乌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关中乌氏。
古陇山地区(今六盘山)水甘草丰,适宜发展畜牧经济。乌氏族中有一个叫“倮”的年轻人,羌语呼壮士叫“阿倮”,有雄心壮志,利用六盘山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养牛牧马,发展畜牧,在昭王城西北一直到大河东岸,差不多十万顷土地的牧场中,蓄养牛羊马匹。对此,倮并不满足,一直盼望自己的牲畜业能迅速增长。
一次,逢集的日子到了,倮像往常一样赶着牛羊到集市上售卖。然而,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往日那种人喧马啸的热闹景象不见了,场地上空空如也,一片寂静。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才知道,集市遭到了“戎王”的抢劫,被官府取缔了。所谓“戎王”,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王爷。当时,因为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中原地区各国往往对少数民族采取“禁运”政策,不许内地商人随便和少数民族进行交易。如,秦国实行外邦人贸易登记制度,《秦律》规定:“客未布吏而与贾,赀一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中原地区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经常带领人马到中原地区的集市上抢劫。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原各国对民族通商的疑虑,所以,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很难看到中原各地的特产。同样,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如良种马和各种畜产品等,在中原各地也成了不可多见的“上品”。
这件事启发了倮。他想戎人只会放牧,而不懂养蚕、织丝。如果自己把马、牛、羊卖给关中农耕地区的农民,收购丝绸和日常生活用品、珍奇珠宝,带回来销往牧区,再换回牲畜销到内地农区,进行循环贸易,肯定能发大财。于是,他决心利用区域经济结构的产品差异,从事边地互补性贸易。他立即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牲畜,并把卖牲畜得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中原的丝绸和少数民族地区缺少的珍稀物品,然后偷偷运进少数民族地区。为了顺利进行贸易,他动脑筋取悦“戎王”,采取了进献的方式。“戎王”看着倮进献的五颜六色的丝绸和其他珍稀物品,果然十分高兴,立即命令照价以赏赐的形式回赠给倮良种马和牛羊。由于当时乌氏倮送给戎王的丝织品通过戎王与西域、中亚各国的商人转手交易,这种贸易是以缯帛、金属铁器换取游牧部落的牲口、皮毛等。西域再往西就是塞人,塞人在春秋时期被月氏人打败,往西迁徙到中亚地区,部分塞人则前往黑海附近,后与在黑海附近的古希腊人建立了关系。而秦国的缯帛、金属铁器则是通过河西走廊被塞人以游牧的方式将从戎王手中得到的物品转销给古希腊人。这种转手贸易,中间利润特别大,所以戎王的回赠就特别丰厚,倮的盈利少说也是成本的10倍。
这次交易的成功,让倮很受鼓舞。他决心继续这种贸易关系,保持和“戎王”之间的易货交易。回到家里后,他立即卖掉所换来的全部马匹和牛羊,再一次到少数民族地区向“戎王”进献丝绸和其他手工业品。“戎王”也像以前一样,以赏赐的形式回赠给倮马匹和牛羊。几次交易后,倮成了当地著名的大牧主。倮的牲畜漫山遍野,不计其数。据史料记载,他的牲畜多到只能用“山谷”进行计算的程度,就是说计算他的牲畜数量已经不是用有多少匹马、多少头牛、多少只羊来计算,而是用他有多少山谷马、多少山谷牛、多少山谷羊来计算。故而他在北地的威望之高,连县令也比不上,他在乌氏县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堡,名为乌氏堡,有仆数千人。
倮发财富有后,懂得巩固边地安宁对自己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为此,他不断向官府提供大量良种马,受到官府的嘉奖。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巡视陇西、北地郡,途经六盘山地区时,耳闻目睹了乌氏倮经商发展畜牧的事迹,当即给倮以“比封君”(接受封邑的贵族)的优待,让倮享受较高的政治待遇,使他以一介牧夫的身份,可以和文武大臣一起,按时进宫朝拜皇帝。
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作为一个牧主与商人,乌氏倮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少见的,相当于后世的“红顶商人”。秦始皇一生一共只封赏了两个平民为君,一个是乌氏倮,另一个是巴寡妇清,足见秦始皇对他的格外恩宠。
三、乌氏倮的经营经验
乌氏倮以一介边地牧夫而成为可比封君的“红顶商人”,是陕西特殊的地域优势造就了他的一生事业。
首先,以货易货,沟通农牧,赚取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乌氏倮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本能的感受到区域经济结构产品单一性带来的交换机会,利用农牧之间的产品差异,进行以货易货的循环交易,为自己掘得了发财致富的第一桶金。陕西是处于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接合部的交换高端地区,这两个经济板块之间由于资源的特殊性使得产品单一性特别突出,各自对对方产品需求的数量巨大,决定了处于两大经济版块接合部的陕西,一定是出大商人的地区,因为他们的商贸活动不是仅仅为小民养生送死服务的小商小贩,而是为调剂民族经济余缺服务的大生意,这就是《货殖列传》所说,陕西“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株邑(今临潼),栋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道理。乌氏倮看到边地少数民族只知放牧牛羊,而不会蚕桑纺织,内地农夫勤于耕桑,而缺乏牧养大牲畜的天然条件,两者都需要交换来互补所需,使他捕捉到了市场需求的巨大缺口,便从边地互补贸易入手,开始构建自己的财富帝国。这是一个精明商人应有的眼光和视角。
问题如果这样简单,乌氏倮就充其量是一个农牧兼营的商人,而不会得到秦始皇的册封。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人们的历史活动都是在他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④。乌氏倮没有想到,当他想方设法与边地的戎王交好关系,用贡献物品来取悦戎王时,正好适应了一个巨大贸易链条的需求。因为戎王得到乌氏倮贡献的丝绸、农产,除了自己享用外,更多的是依此来从河西走廊的塞人手中交换金币和西方产品,塞人又转手将其贩运到中亚细亚乃至罗马换取金币,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外贸易链条。通过这个链条,罗马的金币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而当时崛起的秦国,地处中原,正需要内敛钱财,外拓疆土,乌氏倮的活动恰恰适应了这种国家需求,因此才被秦始皇看重,册封为“封君”,秦始皇册封平民,是从国家需求的大眼光出发的。他册封巴寡妇清,是因为巴寡妇清不仅出钱财助修长城,更重要的是巴寡妇清掌握着修长城所需要的土木建筑技术和冶炼铜人的高端技术,秦始皇才为之修“怀清台”。同样,乌氏倮的活动正好满足了秦国外向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秦始皇才破天荒封他为比君,与文武大臣一道参见皇帝。乌氏倮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治生活动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和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起了历史的前驱作用。
其次,满足国家需要,为和谐边疆贡献力量。乌氏倮的成功在于他有大眼光,把自己的经贸活动与国家需求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结好戎王贡献丝绸,是不自觉催动了欧亚商品交换的链条,那么,他发财致富后,不断向官府提供良马,就是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最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需物品,而良马都在西北的草原之上,春秋时期国家的强盛是以良马作为标志的,能否有“战车千乘”,是国家军事实力的显示,而乌氏倮贡献的良马,正好满足了秦帝国拓土开疆对战马的需求,怎能不引起秦始皇的好感和宠幸。同时,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时期,边疆少数民族的马队是中原以农耕为主的平和民族最难对付的事,他们为了取得中原的产品,常常铁骑南下,使中原王权难以应付,秦修长城、汉初和亲都是对草原铁骑无奈的举措。而乌氏倮用交换的手段满足了戎王所代表的少数民族的需求,使他们不至于上马劫掠,这就为保持边疆的和谐与安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功劳不在出策安民的文臣和上阵操戈的武将之下,秦始皇才封他为君,准许他与文武百官同列。
社会历史是多元集合的过程,经济活动的背后常常是政治活动,商务就是政务。乌氏倮以博大的胸怀与历史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一开始就显示了秦商“以国事为重”的价值取向和作为“国商”的历史地位。
①参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劳蜍:《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
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卷。
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卷。
④《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封君筑台,礼抗千乘,
牧长穷山,惟商显荣,
嗟我耕战,萤萤其功,
耕者功,战者功,
商者独萤萤。
有国法,有王命,
解我年馑者何无功。
这首秦国当时流传的民谣,说明秦汉时期陕西处于中国农耕经济与西部畜牧经济交换的顶端,两种经济结构各自产品的单一性使这一地区成为交换性最强的地区。利用这一区域优势,乌氏倮“牧长穷山,惟商显荣”,在经营边地贸易中“封君筑台,礼抗千乘”,成为秦代受秦始皇册封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一、秦汉西北的边地贸易
华夏民族最初是以黄河流域为活动范围,而这些地方整个是黄土地带,广袤而又肥沃的土地,使人们得以从事农业生产。黄土地带虽不适于森林的滋植,但宜于作牧地,黄土地上滋生细草,宜于畜类的繁殖。不过中国古代的畜牧还不是很发达,大约到西周末年,牲畜在农业经济当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春秋时代,所谓中原一带还是华夷杂居,以农耕为主,农业在黄河流域已很普遍。当时的中国,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北方包括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以及河西一带地方,属于畜牧经济区;江淮以南秦岭区域和陇西,都算是森林经济区;中间以“三河”为中心连同关中以及蜀和广汉两郡一带地方,构成精耕农业经济区;这三个区域,代表着三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三者的互相竞斗,充满了春秋战国,尤其是秦汉帝国时代的历史。
秦汉帝国内部的物产分布,受三大经济区域板块的影响,各自都有极强的产品单一性。西北一带所出产的主要是畜牧产品,如马畜、皮革、筋角、旃裘之类,所以说“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而中原农业经济区,对马匹和裘革极感需要。反之,畜牧民族所希冀中原的除了酿酒用的蘖秫、谷米之外,对中原的丝织品具有极大的需求,为了获得这些他们生产不了的产品,畜牧民族常常兴兵劫掠。双方这种经济上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所以西北边界的滋扰始终不得休止。汉帝国的后半期,终于演成畜牧民族的大侵入,倾覆了汉帝国。
中原农业经济区域的出产,主要是农产品,除此外值得称道的就是淮河上游漆和齐鲁一带的蚕桑。关于古代汝颍一带产漆,据《禹贡》,豫州和兖州的贡品当中,都有漆。《周礼·职方》讲豫州的出产,也提到漆。《货殖列传》列举可以与千户侯相等的财产时,也特别举出“陈夏千亩漆”。可知在那时候,这一带地方是漆的主要产地。太史公所说,有漆千斗,可比千乘之家,可见漆是当时大宗出产和中原的一大富源。而其间最具重要性的要数蚕桑。蚕桑到秦汉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主要经营蚕桑业的,要算是土宜桑麻的齐鲁卫梁宋一带,①而以临淄和襄邑为中心。《左传》晋公子重耳将去齐,谋于桑下,蚕妾闻之,似乎当时齐国上下,都习于此业。丝织品的消费者主要是当时少数的贵族。孟子说:“五十者可以衣帛”,还是一种奢望。《盐铁论》上说:“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知古代一般平民的衣料乃是麻布。丝织品的销路,当时主要是西方的夷狄诸国,不仅贵族本身,连他们的奴婢也都穿着锦帛绫罗。所以,秦汉之际,岁赐匈奴和历次出使所携,都是以丝织品为主。另外,当时的经济生活,大体是家庭自给自足,平民自己所需的麻布全归自家织作,只是偶然出现于市场。反之,丝织品的生产者,除了官府特别所需外,完全是为市场生产,因此,丝织品成为当时的另一大宗主要商品。后来随着汉帝国的势力和声威,这种制造品沿“丝路”一直销到西域诸国,最远到了罗马。
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当时蚕桑与皮革之间的交换,成为西北边地贸易的主要内容,将中原的丝绸贩运到边地,再将边地的皮革贩运到中原,在丝绸与皮革的对流中,赚取大量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是最能发财致富的经营项目。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正确指出:“孝文、德、缪居雍(今凤翔),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株邑(今临潼),栋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②,说陕西是出大商人的地方。而移民到边地的乌氏倮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秦商的一般面貌。
二、乌氏倮的经营概况
《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乌氏倮的经营状况有所记载: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③
据此可知,乌氏倮是乌氏(或“兀者”)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乌氏最初是中原族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相传少昊作东夷部族首领时,以鸟名任命职官,有“乌鸟”一职,其族徽为大乌,族中有姓氏为“乌鸟氏”者,专职负责掌管高山丘陵。春秋战国时期,朝廷迁徙中原人民实边,乌鸟族逐渐西移,陇西地区有乌氏国(今宁夏六盘山),是西戎民族义渠戎部族的一个分支。乌氏国被秦国攻灭后,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在乌氏戎族的主要居牧地设立乌氏县(今固原南部与甘肃平凉北部一带),其国人中有以故国名为姓氏者,就称乌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关中乌氏。
古陇山地区(今六盘山)水甘草丰,适宜发展畜牧经济。乌氏族中有一个叫“倮”的年轻人,羌语呼壮士叫“阿倮”,有雄心壮志,利用六盘山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养牛牧马,发展畜牧,在昭王城西北一直到大河东岸,差不多十万顷土地的牧场中,蓄养牛羊马匹。对此,倮并不满足,一直盼望自己的牲畜业能迅速增长。
一次,逢集的日子到了,倮像往常一样赶着牛羊到集市上售卖。然而,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往日那种人喧马啸的热闹景象不见了,场地上空空如也,一片寂静。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才知道,集市遭到了“戎王”的抢劫,被官府取缔了。所谓“戎王”,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王爷。当时,因为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中原地区各国往往对少数民族采取“禁运”政策,不许内地商人随便和少数民族进行交易。如,秦国实行外邦人贸易登记制度,《秦律》规定:“客未布吏而与贾,赀一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中原地区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经常带领人马到中原地区的集市上抢劫。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原各国对民族通商的疑虑,所以,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很难看到中原各地的特产。同样,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如良种马和各种畜产品等,在中原各地也成了不可多见的“上品”。
这件事启发了倮。他想戎人只会放牧,而不懂养蚕、织丝。如果自己把马、牛、羊卖给关中农耕地区的农民,收购丝绸和日常生活用品、珍奇珠宝,带回来销往牧区,再换回牲畜销到内地农区,进行循环贸易,肯定能发大财。于是,他决心利用区域经济结构的产品差异,从事边地互补性贸易。他立即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牲畜,并把卖牲畜得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中原的丝绸和少数民族地区缺少的珍稀物品,然后偷偷运进少数民族地区。为了顺利进行贸易,他动脑筋取悦“戎王”,采取了进献的方式。“戎王”看着倮进献的五颜六色的丝绸和其他珍稀物品,果然十分高兴,立即命令照价以赏赐的形式回赠给倮良种马和牛羊。由于当时乌氏倮送给戎王的丝织品通过戎王与西域、中亚各国的商人转手交易,这种贸易是以缯帛、金属铁器换取游牧部落的牲口、皮毛等。西域再往西就是塞人,塞人在春秋时期被月氏人打败,往西迁徙到中亚地区,部分塞人则前往黑海附近,后与在黑海附近的古希腊人建立了关系。而秦国的缯帛、金属铁器则是通过河西走廊被塞人以游牧的方式将从戎王手中得到的物品转销给古希腊人。这种转手贸易,中间利润特别大,所以戎王的回赠就特别丰厚,倮的盈利少说也是成本的10倍。
这次交易的成功,让倮很受鼓舞。他决心继续这种贸易关系,保持和“戎王”之间的易货交易。回到家里后,他立即卖掉所换来的全部马匹和牛羊,再一次到少数民族地区向“戎王”进献丝绸和其他手工业品。“戎王”也像以前一样,以赏赐的形式回赠给倮马匹和牛羊。几次交易后,倮成了当地著名的大牧主。倮的牲畜漫山遍野,不计其数。据史料记载,他的牲畜多到只能用“山谷”进行计算的程度,就是说计算他的牲畜数量已经不是用有多少匹马、多少头牛、多少只羊来计算,而是用他有多少山谷马、多少山谷牛、多少山谷羊来计算。故而他在北地的威望之高,连县令也比不上,他在乌氏县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堡,名为乌氏堡,有仆数千人。
倮发财富有后,懂得巩固边地安宁对自己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为此,他不断向官府提供大量良种马,受到官府的嘉奖。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巡视陇西、北地郡,途经六盘山地区时,耳闻目睹了乌氏倮经商发展畜牧的事迹,当即给倮以“比封君”(接受封邑的贵族)的优待,让倮享受较高的政治待遇,使他以一介牧夫的身份,可以和文武大臣一起,按时进宫朝拜皇帝。
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作为一个牧主与商人,乌氏倮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少见的,相当于后世的“红顶商人”。秦始皇一生一共只封赏了两个平民为君,一个是乌氏倮,另一个是巴寡妇清,足见秦始皇对他的格外恩宠。
三、乌氏倮的经营经验
乌氏倮以一介边地牧夫而成为可比封君的“红顶商人”,是陕西特殊的地域优势造就了他的一生事业。
首先,以货易货,沟通农牧,赚取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乌氏倮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本能的感受到区域经济结构产品单一性带来的交换机会,利用农牧之间的产品差异,进行以货易货的循环交易,为自己掘得了发财致富的第一桶金。陕西是处于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接合部的交换高端地区,这两个经济板块之间由于资源的特殊性使得产品单一性特别突出,各自对对方产品需求的数量巨大,决定了处于两大经济版块接合部的陕西,一定是出大商人的地区,因为他们的商贸活动不是仅仅为小民养生送死服务的小商小贩,而是为调剂民族经济余缺服务的大生意,这就是《货殖列传》所说,陕西“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株邑(今临潼),栋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道理。乌氏倮看到边地少数民族只知放牧牛羊,而不会蚕桑纺织,内地农夫勤于耕桑,而缺乏牧养大牲畜的天然条件,两者都需要交换来互补所需,使他捕捉到了市场需求的巨大缺口,便从边地互补贸易入手,开始构建自己的财富帝国。这是一个精明商人应有的眼光和视角。
问题如果这样简单,乌氏倮就充其量是一个农牧兼营的商人,而不会得到秦始皇的册封。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人们的历史活动都是在他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④。乌氏倮没有想到,当他想方设法与边地的戎王交好关系,用贡献物品来取悦戎王时,正好适应了一个巨大贸易链条的需求。因为戎王得到乌氏倮贡献的丝绸、农产,除了自己享用外,更多的是依此来从河西走廊的塞人手中交换金币和西方产品,塞人又转手将其贩运到中亚细亚乃至罗马换取金币,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外贸易链条。通过这个链条,罗马的金币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而当时崛起的秦国,地处中原,正需要内敛钱财,外拓疆土,乌氏倮的活动恰恰适应了这种国家需求,因此才被秦始皇看重,册封为“封君”,秦始皇册封平民,是从国家需求的大眼光出发的。他册封巴寡妇清,是因为巴寡妇清不仅出钱财助修长城,更重要的是巴寡妇清掌握着修长城所需要的土木建筑技术和冶炼铜人的高端技术,秦始皇才为之修“怀清台”。同样,乌氏倮的活动正好满足了秦国外向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秦始皇才破天荒封他为比君,与文武大臣一道参见皇帝。乌氏倮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治生活动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和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起了历史的前驱作用。
其次,满足国家需要,为和谐边疆贡献力量。乌氏倮的成功在于他有大眼光,把自己的经贸活动与国家需求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结好戎王贡献丝绸,是不自觉催动了欧亚商品交换的链条,那么,他发财致富后,不断向官府提供良马,就是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最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需物品,而良马都在西北的草原之上,春秋时期国家的强盛是以良马作为标志的,能否有“战车千乘”,是国家军事实力的显示,而乌氏倮贡献的良马,正好满足了秦帝国拓土开疆对战马的需求,怎能不引起秦始皇的好感和宠幸。同时,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时期,边疆少数民族的马队是中原以农耕为主的平和民族最难对付的事,他们为了取得中原的产品,常常铁骑南下,使中原王权难以应付,秦修长城、汉初和亲都是对草原铁骑无奈的举措。而乌氏倮用交换的手段满足了戎王所代表的少数民族的需求,使他们不至于上马劫掠,这就为保持边疆的和谐与安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功劳不在出策安民的文臣和上阵操戈的武将之下,秦始皇才封他为君,准许他与文武百官同列。
社会历史是多元集合的过程,经济活动的背后常常是政治活动,商务就是政务。乌氏倮以博大的胸怀与历史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一开始就显示了秦商“以国事为重”的价值取向和作为“国商”的历史地位。
①参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劳蜍:《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
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卷。
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卷。
④《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