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
作者:王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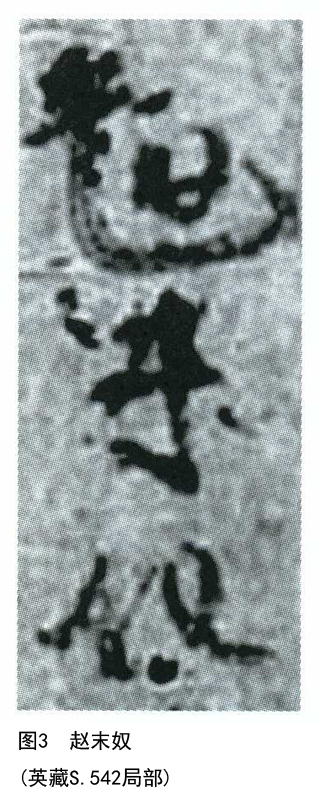

synpyn新平(《史君墓志》)
2003年西安出土的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史君墓志》的独特性在于铭文由汉语、粟特语两种文字构成,记录了一个由史国入华的粟特人的生平仕履与家族概况,提供了许多新知。如果说这是一篇“双语”铭文,那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粟特文、汉文两个文本并不是对译的,脉络虽大体平行,细节内容却互有详略,尤其发人兴味。粟特文部分已经由吉田丰教授作出通篇解读①。笔者曾对这篇“双语”铭文反复学习,受益匪浅。在此愿意不揣谫陋,就几个枝节问题贡献一点初步意见,向通人请益。
粟特文部分第10~11行,讲述史君妻康氏的出生地:ZKh kty-"βr synpyn z’t(c)h“His wife was born in Senpen(其妻室生于Senpen)”。地名Senpen,吉田丰推测为距离姑臧(今甘肃武威)西南不远的西平(今青海西宁)。这个推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粟特文墓志里说,史君“家于姑臧”。同样作为入华的昭武九姓后裔,其妻康氏家族寓居西平,实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据“粟特古信”第5号记载,最迟到4世纪初,金城(今甘肃兰州)已经进入粟特商胡的活动范围。吉田先生还特别提示固原出土的《史射勿墓志》中的一个细节:史射勿的父亲任鄯州刺史,鄯州正是唐代的西平郡。这个暗示的指向有二:姑臧史君家族与固原史射勿家族的可能性关联,也就是说,史君的次子维摩(碑文中对应的粟特语名Zhe-matvandak,按严格音译即是射勿)与史射勿是否为同一人;在此基础上,如果这个同名人意味着同一人,那么史君家族跟西平的关联就加深了一层。不过,吉田先生很谨慎,没有仅就一个姓名的重合来断论两组铭文的同名人即是同一人。同时,他也很坦率地指出,西平的中古音*siei b'iw*ng跟粟特文的Senpen相较,前一个字的鼻音-n韵尾并不密合。
笔者有一个猜测,Senpen有可能是新平,即北周时期关中的新平郡(郡治在今陕西彬县)。首先从音理上说,新平*sien b'iw*ng与Senpen勘同,没有窒碍。从地理观之,《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泾州(2618页):“新平郡后汉献帝建安中置。”后魏时又置郡,北周因之。《周书》卷三四(594页):保定四年(564年)韩盛出为新平郡守,是其证②。新平是丝绸之路干道经原州、泾州抵达长安前最后一个要地,为长安西北之门户,两地相距不过百余公里③。从事理上看,把新平纳入考虑范围,跟汉文、粟特文墓志的记述也没有牴牾。反之,西平在北周时期名为乐都郡,却是西平说的一个困难之处。《史君墓志》为580年写镌,记录史君夫妇于519年在Senpen结为连理,至史君夫妇去世,一生经历北魏、西魏和北周三朝,在这期间确实有新平这样一个地方。史君夫妇最后终老于长安,表明他们在婚后某个时间从新平迁居都城。
寓居新平一带的粟特人,不止康氏一家。跟史君生平足迹相仿的可以举唐代的安令节为例。据唐神龙元年(705年)《安令节墓志》,其“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北图拓本汇编,第20册,6页)。豳州宜禄(今陕西长武),贞观二年(628年)分新平置宜禄县(《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关内道邠州上,967页)。邠州、宜禄两地距离约40公里。
如果对《史君墓志》的地名Senpen即新平的比定是正确的话,则我们可以确信,史君、安令节两个昭武人家进入中原的路径完全一致。这表明,在北朝至隋唐时期,新平在粟特胡人迁徙与聚落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线索值得继续注意④。
二 富卤多(《史君墓志》)
《史君墓志》汉文部分的最后,有史君夫妇的诸子列名。因为碑面有所损毁,部分字迹难辨,其中第三子名字的第二个字,发掘整理者的正式录文阙释:“富□多”⑤。粟特文部分该名写作pr'wtβntk(Pro-tvandak)⑥,这应该是森安孝夫先生凭借铭文残画将此名补释为“富卤多”的根据⑦。富卤多*p’i*u luo ta对应于pr’wt,音韵上完全成立。
富卤多这个名字形式在现有的吐鲁番、敦煌中古人名资料里未见。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天授二年(691年)文书中,有一位佃人名康富多(大谷文书2375号,大谷集成Ⅰ/89)。“富多”是否有可能是“富卤多”的简写?同名的人物出现于黄文弼得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的一方唐神龙元年(705年)的墓志,墓主人康氏,其夫名康富多(黄文弼《高昌专集》增订本,158页)。基于两件史料年代接近、大谷文书多有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墓葬文书这一事实,可以推断两处的康富多很可能是同一人。敦煌出P.4907《庚寅年(903年?)九月十一日至辛卯年七月九日诸色斛斗支付历》行2有曹富多(唐耕耦、陆弘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205页读“曹富员”)。另外,唐先天二年(713年)的一件军事文书里的“刘富多”(TCW Ⅳ/8)。武周时期西州的《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的一个男性奴隶名“富多”(TCW Ⅲ/525),在同一件名籍中,有相当多的非汉语名字,这也许可以作为推测富多的胡奴地位的线索。这几例富多,可与富卤多一并参考。
富卤多的粟特语全名为Protvandak。他的两位兄弟的名字,也都有Vandak这样一个常见的男性名字构成成分,意思是“奴仆”,但是,《史君墓志》的汉文部分均将Vandak省略未译。这个名字在汉文里一般音写为“盘陀”。所以若对Protvandak加以完全汉译,则这个名字可以写成“富卤多盘陀”或“富卤多奴”。吐鲁番写本中有一个名字“索富奴”(《唐某寺旅帅杨文俊等马匹簿》,TCW Ⅳ/349),是否有可能是Protvandak的音义合璧的缩写译名呢?索固然不是胡姓,但是中古河西的民族融合生活中,汉姓之人接受胡名的例子比较多见,这种汉姓胡名现象所透露的汉胡文化交相互化(acculturation)的本质,亟待进行专门的研究,在此姑不深论⑧。
在富卤多=Prot(vandak)这一对音资料发现之前,昭武九姓人“富奴”一名最直接的比定还属粟特语rywβntk(UpIn Ⅱ,68),“富”“奴”是一个完全的意译。ryw“富庶(之神)”是粟特人命名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字眼,汉语音译方式有“了”、“阿了”、“阿塯”、“阿溜”、“阿留”、“阿僚”等等。据崔令钦《教坊记》,唐玄宗时宫廷有多种外来舞蹈,其中的“健舞”《阿辽》(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4,34~35页),或许即与ryw有关,是一种来自粟特地区的舞蹈。
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不六多”现在也可以与《史君墓志》的Prot(vandak)相比定:
车不六多《高昌义和六年(619年)伯延等传付麦、粟、*(外广里禾)条》,TCW Ⅰ/355。娶妻。
车不吕多《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TCW Ⅰ/450-452。买丝。
安不六多《唐保人安不六多残契》,TCW Ⅲ/301。契约作证。
□不六多《□不六多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TCW Ⅰ/461。
从中古音看,不六多*p'i*u liuk ta,不吕多*p'i*u liuk to,音值一致,则车不六多、车不吕多显然同名。是否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的名字的不同写法?若然,称价钱文书的大体年代即可因保留高昌义和六年(619年)纪年的伯延文书得到大致的推定⑨。车,吐鲁番本地旧族车师人的“国姓”⑩。一般而言,车师人经过数百年与中原的种种交往,当时汉化程度已经比较高。然而,写本中保留下来的车不六多、车不吕多的名字透露出7世纪顷伊朗文化对世代居住在天山东段的车师后代影响的存在。
□不六多应是高昌国晚期的人物,而安不六多则生活在唐朝治理西州时期。另外,武周时期西州官府编制的一个部曲客女奴婢名籍中,有一个客女名石多不六(TCW Ⅲ/527),有可能是汉人书吏因不解胡语,将“不六多”误倒而致。安、石两姓均在传统的昭武九姓之列,用粟特语不六多为名,理有宜然。
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Protvandak与富卤多出见于580年长安的碑铭,不六多、不吕多稍晚,行用于7~8世纪的吐鲁番盆地。《史君墓志》作为解读不六多一名的钥匙,丰富了我们对粟特人名及其汉写方式复杂性的知识,这也是双语铭文的特别价值所在。
三 莫潘(《虞弘墓志》)
墓志云:“公讳弘,字莫潘。”研究者曾有猜测,莫潘这个名字不是汉名,但提出具体解诂方案的似乎只有两家。林梅村教授对莫潘有如下解说(11):
我们怀疑,其名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bayaspān(主使、神使),像是个火祆教徒的教名。
卓鸿泽先生撰《〈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中三胡名拟测及粟特胡、丁零胡问题》(12)一文,对莫潘的原语发表了如下意见:
“莫潘”二字似为Pahlavi语mahraspand(火祆月历第廿九日)之对音,用作人名,特隐去词中音节,截取首尾二音,使合乎华民双音名字之常习。
这两种比定,对音与莫潘的中古音构拟*mak p’uan均不契合。从方法上说,两位先生的上述解决方案不同,但取径相似,都是受虞弘曾出使波斯这一线索暗示,向中古波斯语的音近的语汇寻求答案。这本身无可厚非,惜有说无证,是其共同弱点。构拟复原保留在古代汉文文献中的译写外语名字,首先应在合理推测原语的语种归属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汉语古音的线索,尽量寻找实际存在的同类专名,进行对证。胡语解诂如果不以对有关语词的审慎音韵构拟为基础,便很少有达到正确结论的可能。通过增减音节以求勘同,尤应慎重。林先生猜测的“莫潘”原语bayaspān,应该是摘引白D.N.MacKenzie著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7页)的词条,林先生所提供的语译“主使、神使”云云,跟该字典的原有释义“messenger,envoy”(信使、使者)相较,距离较远,不免有增字解经、强经就己之嫌。
卓先生的假说引及中世波斯语mahraspand,释义“火祆月历第廿九日”是通常说法(参见H.S.Nyberg,Hilfsbuch des Pehlevi,Ⅱ,Glossar,Uppsala 1931,143页),其实查核一下中古波斯语人名的工具书,这个词用为人名的例子并不少(见Ph.Gignoux,Noms propres sassanides en moyen-perse épigraphique,Wien 1986,No.567 Māraspand条),本可以为他的假说提供实际使用的人名例证。摩尼教术语中也有这个字,中世波斯语摩尼教词汇中mhr'spnd在《残经》里音写作“摩诃罗萨本”(13)。按照卓先生的说法,莫潘这个名字乃是截取首尾两个音节“摩”、“本”*mua pu*n而成。但是,使用如此大刀阔斧的简化音译解释,未免武断。
实际上,莫潘*mak p‘uan是粟特名m’xprn的准确音写。最早对证出这个粟特名的汉文音写形式的是Dieter Weber先生,所举例证是九世纪初某戌年敦煌诸寺丁壮车牛簿(S.542)中出现的寺户曹莫分*mak pi*un(14),对音字与原语音值密合。莫潘不过是使用同音字的别译。要之,—语源的问题早已解决。
“莫”、“潘”两个字,在粟特语汉文转写词中代表的音值与译词的对应相当稳定,在其他名字的转写中有系统的表现,如:演莫(TCW Ⅰ/359)*jiεn mak=y’nm’x(15),以及后文将要讲到的莫鼻、莫毗、莫毗多等;康演潘(TCW Ⅲ/539)=y’nprn(UpIn Ⅱ,81),曹提始潘(TCW Ⅰ/359)* d’iei si p‘uan=*δ(y)scyprn(16)。
莫潘这个名字并不仅仅见于《虞弘墓志》。唐西州时期《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707年)中有一户主名何莫潘,其年80岁(TCW Ⅲ/535)。同一个名字,还见于大谷文书4152号行4(大谷集成Ⅱ/208)(图1),整理者读为“何羌潘”。该残片纸面有褶皱,字为草体,“羌”应释“莫”。该户等文书内容跟点籍样相关,两件文书所记如果是同一人,则大谷文书4152的年代也应该是8世纪初。
四 默奴、末奴、莫奴与莫女(吐鲁番写本)
借此机会顺便讨论一下“默(*m*k)奴”、“莫奴”及“末(*muat)奴”,三种形式都来自同一个粟特名字:m’xβntk“月(神)之奴”,前半是m’x的音写,后半是βntk的义译(17)。
(1)翟默奴(大谷2848,大谷集成Ⅰ/114)。
(2)宋默奴(图2)(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图42;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153页定为《圣历二年(699年)西州勘检田籍簿》),旧读“点奴”(18)。这件文书是用流利的行书写成,“默”字的“犬”旁末笔向下撇,是因为联笔的笔势关系,似非“占”字。所以,笔者倾向于把它读成“默”。
(3)安末奴(《唐载初元年(689年)三月某团卫士安末奴等欠十驮马价凭》(19);TCW Ⅱ/306;大谷3026,末字,大谷集成Ⅱ/6作“未”)。三件文书中的安末奴是否为同一人,俟详考。
(4)赵末奴(Or.8212/542v,Ast.Ⅲ.4.091《武周西州赵延愿等得冯酉武田亩帐》)(图3),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136页)读为“赵未如”,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卷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3页)读为“赵于奴”。前一字写本中的确写作“未”,第二字左旁笔路不清,右侧应是“又”。联系起来读,不难令人想到吐鲁番的常见粟特名“末奴”。“未”、“末”字形相近易混,特别是在外国语译音名词中出现的情况下,如果传写者不通来源语,碰到模棱两可的字形,往往抄错。例如,在摩尼教《下部赞》《叹明界文》一节中,署名为作者的摩尼弟子末冒(Mār Ammō),即错写成“未冒”。参W.B.Henning为Tsui Chi英译《下部赞》所写的补记,BSOAS,Ⅺ(1943),216页注4。
(5)陈莫奴。见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前后西州高昌县欠田簿》(大谷4042,籍帐研究,398页;大谷集成Ⅱ/192)(图4),整理者读为“陈英奴”,“英”实应读“莫”。这个字在文书上有涂改的痕迹,似乎是先写成“英”,后来校对时有补笔。
(6)张(?)莫奴(图5)。无独有偶,伯希和库车汉文文书146号名籍残片中有一个名字,整理者Trombert教授读为“张(?)英奴”(20)。两件名籍出自不同地方,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书手在“莫”字上都不很确定,估计致误的原因是不懂胡语的汉人官吏在造籍的时候,将汉文化命名习俗里不常见的“莫”误认为“英”(21)。张(?)莫奴、陈莫奴都是汉姓胡名的人物,如前揭“索富奴”一样,提供了唐代前期中国支配西域时期汉姓之人接受外族命名方式影响的例子。
(7)莫女。女性人名中也有以“莫”为构成因素的例子,如吐鲁番出土《唐何延相等户家口籍》残片之二(TCW Ⅱ/34)户主曹僧居尼与其妻安氏的五岁女儿曹莫女(图6),整理者读为“英女”。父母双方曹、安都是昭武九姓人,为孩子取本文化的名字是合乎情理的。粟特语女性人名留存下来的不多,目前可以找到跟莫女接近的有m’xδ’yh“月神之婢”(22)。也有可能莫女是一个混合语名字(hybrid name),由粟特语的“莫”m’x与汉语的“女”,取名的命意是“莫日(所生)之女”。
五 君陁(《虞弘墓志》)
《虞弘墓志》(592)的碑石右下角残缺,造成墓志的第1~9行有若干字的阙文,影响铭文的通读,特别是第2~3行叙述虞家先世的一段:
……弈叶繁昌,派枝西域,倜傥人物,漂注□□□□/奴栖,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陁,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
从志文文例推测,父亲之前必是祖父,鱼国领民酋长是其任官,“奴栖”应是名字或名字的一部分。从用字看,奴栖应该不是汉语,但因为其前文字残断,给复原带来困难。
既然虞弘的“字”莫潘有粟特语源,其父的名字首先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推求。君陁*ki*un da,从音韵上看,与粟特行客题壁中的人名kwnt(UpIn Ⅱ,p.54)颇为接近。kwnt似乎是一个常见的粟特名字,Sims-Williams UpIn词表中著录8例,属于行客题铭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该词的语源本义不明。在铭文的释读上,Humbach读为kwzt。对此异读,参见Pavel B.Lurje,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Wien: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10,No.587,也是以kwnt形式为词条,而在释议中兼及Humbach的kwzt读法。从汉文语料角度看,kwnt的读法有对证。
如果上述对《虞弘墓志》两个粟特名字的考证可以成立,则有关虞弘家族的族属问题判定便可以获得一个语言学的支撑点。迄今为止,有关虞弘的族属,学术界争论热烈,有西胡说(荣新江:“西北民族”、罗新:“粟特”)、柔然说(罗丰)、稽胡说(林梅村)、月氏说(周伟洲)、回纥说(杨晓春)等。如果虞弘父子的名字君陁、莫潘的粟特语源可以确定,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这一表征是否暗示虞氏的母语背景?或者至少可以推论,当时他们生活在一个以粟特文为主导文化的环境。此点对《虞弘墓志》中的另外两个难题——籍贯“鱼国”、出生地“尉纥驎城”——的解答或许都将有连带的影响。
六 莫鼻(《康阿达墓志》)
张维《陇右金石录》(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1943年)第二卷首次著录,有完整录文。张氏在一些字的读法上表示踌躇不决。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贞观182,124页)收录该墓志,全文照录张维旧本。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1期)讨论该件史料,有部分录文。作为《武威市地方志丛书》之一的《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62~63页)收录了这件墓志的拓片与录文,但照片尺寸过小,大部分的字无法辨识。该书的体例一般著录碑碣的存佚情况,但此件除抄录张维的按语外,并无其他说明。
康阿达墓志原石现藏武威博物馆,陈国灿先生曾经前往查阅,在其前揭论文的改订版中,注明“此处所引志文,乃笔者临石手录”,公布了部分修正录文(23)。陈先生所作录文对旧录文有改进,如他将墓志录作《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鼻息阿达墓志铭》,“莫鼻”纠正了既往的误读“莫量”(24)、“莫覃”(25)。
写本中有例子证实“莫鼻”的读法。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一件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官文书中有“翟莫鼻”一名(26)。敦煌写本《文明判集》(P.3813)讲述一个长安县的判例,富人名史婆陀,穷人名康莫鼻(行116)。可见“莫鼻”一名的写法相当稳定。
莫鼻*mak b’ji,即粟特人名m’xβy’rt(Mākh-vīrt)的音写,意为“得自月神”或“莫日所得(的孩子)”,“莫日”粟特七曜历每周七天中的一天。
粟特名m’xβy’rt还有其他转写方式:(曹)莫毗(《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TCW Ⅰ/359,在同一件文书中,该名共出现三次,不知是三人同名,还是重复误收);(康)莫毗多(TCW Ⅰ/450),均已由吉田丰考出(27)。
七 琼根(《康阿达墓志》)
《陇右金石录》录文有“丧兹英喆,往投琼银”一句。对“琼银”这个罕见词,录文者张维先生本人也表示存疑。夏鼐先生推测,这个词“疑有祆教中死者所居冥府之译音”(28)。案:《武威金石录》所附拓本模糊,大部分字迹漫漶,仔细辨认,该字右旁的“艮”似无问题,左侧部首笔路不清。中古墓志中常见“琼根”一词,比喻出身高贵,例如:
禀质琼根,湛如沧海。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魏沧州刾史王僧墓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4册,图版290。
琼根盘郁,历千载而弥隆。宝叶骈罗,贯终古而独茂。保定四年(564年)《周故开府仪同贺屯植之墓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4册,图版350。
猗哉名哲,赫矣先人,琼根玉干,凤羽龙鳞。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崔德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427页。
琼根宝叶,陪驾东京,乃为河南人也。隋仁寿四年(604年)《马稺妻张姜墓志》,同上书第5册,图版401之2。
假设“往投”二字释读无误,《康阿达墓志》的这句或许本来就是“往投琼根”。但这里的“琼根”跟上引诸志文的用法稍有不同,大意仍是“(死后到阴间)归见先人”。总之,如果在此是“琼根”二字,那么这句话在汉语范围之内可以理会,不必向胡语求解。因笔者未见原碑,拓本不清,旧录文未尽人意,目前只能设论存疑,希望今后有机会落实这一悬案。
引用文献缩写形式说明:
(本文引用中国正史,采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其他古籍除特别指出者外,一般使用四部丛刊本)
北图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BSO(A)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and African) Studies.
大谷集成=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壹一叁,(京都)法藏馆,1984~2003年。
籍帐研究=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
TCW=唐长孺等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UpIn Ⅱ=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I,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2.
XH=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2册,中华书局,2008年。
注:本文系德国学术基金会支持的东方写本研究课题(DFG-Forschergruppe 963)成果之一。
① [日]吉田丰:《两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中华书局,2004年,26~42页。Yoshida Yutaka,“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new Xi’an inscription.”E.de la Vaissière&E.Trombert(eds.),Les Sogdiens en Chine.Paris: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2005,pp.57-72.
②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80年,84页。
③ 罗丰:《北朝、隋唐时期的原州墓葬》第二节〈途经原州的“丝绸之路”〉,《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31~32页。
④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中华书局,2007年,168~169页。
⑤ 孙福喜:《西安史君墓粟特文汉文双语题铭汉文部分考释》,《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中华书局,2004年,19页。
⑥ 这个粟特名字还有另外一种拼法:’prwtβntk,见Sims-Williams,UpIn Ⅱ,41。
⑦ [日]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40页注⑥;Yoshida,“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new Xi’an inscriptlon”,p.61 n.7.
⑧ 实际上,不唯中古时代生活在华北、西北的汉族人曾面临与内亚、中亚、西亚、南亚异文化的深入接触,也有迹象表明,在中国边裔地区的外族之间同样存在着彼此文化的“取”与“予”。有关混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在命名风俗上的体现,请参看P.Zieme,“Hybrid names as a special device of Central Asian naming.”Lars Johanson/Christiane Bulut(eds.):Turkic-Iranian Contact Areas.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6,pp.114-127.
⑨ 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71页。
⑩ 刘铭恕:《吐鲁番文书札记·车师王国的遗民》,《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98~100页,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裦积到车姓人共13例。如果加上大谷文书等其他写本收藏,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11) 林梅村:《稽胡史迹考》,《中周史研究》2002年1期,84页。
(12) 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辑,2009年,科学出版社,75页。卓先生在文中说:“最为关键的胡天方音,迄今无解”。其实,自从《虞弘墓志》公布以来,各种角度的解说尝试相当之多,如张庆捷、荣新江、林梅村、罗丰、周伟洲、罗新、郭平梁和杨晓春等学者都有专文,所论当然也涉及到卓先生感兴趣的三个语词“鱼国”、“莫潘”和“尉纥驎”的语源,发表均在卓文之前。有关篇什的研究综述,请参见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50~73页;现收入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8~110页。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西域研究》2007年2期,113~117页。
(13) E.Chavannes-P.Pelliot,“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JA 1911.p.544 n.1;1913,p.125;吉田丰「汉訳マニ教文献における汉字音写された中世イラン语について」(上)『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Ⅱ(1986),リストNo.56。
(14) Dieter Weber,“Zur sogdischen Personennamengebung”.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77(1972),p.197.
(15) 吉田丰「Sino-Iranica」『西南アジア研究』No.48(1998)、第38页。
(16) 吉田丰「Sino-Iranica」『西南アジア研究』No.48(1998)、第96、242-243页。
(17) m’xβntk的纯音写形式有(曹)莫槃(TCW Ⅰ/359)*mak buan,省略一个音节-tk,完整的音写应该是“(曹)莫槃陀”。此承吉田丰先生教示。
(18) 《周年次未详(690~698年)西州勘官田簿》,籍帐研究,335页。
(19) 旧题《安末奴纳驼状》,参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年,35页。此据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27~128页。
(20) Eric Trombert(ed.),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Paris: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2000,p.115.
(21) “莫”字,古写本、刻本中,当中的“日”常写作“口”,跟“英”字形很接近。在典籍中,“莫”、“英”之讹不一而足,涉及外语转汉的讹误,著名的例子可以举杜佑《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5402页)突厥职官:“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亦呼为英贺弗。”所谓英贺弗,《册府元龟》卷九六二(11319页)作莫贺弗。莫贺弗多见于史籍,《虞弘墓志》铭文也证实莫贺弗是正确的写法。
(22) W.B.Henning,‘Sogdica’,James G.Forlong Fund,Vol.XXI(1940),p.7,并参UpIn Ⅱ,56。
(23) 收入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73~97页,《康阿达墓志》见86页。其实,如果将碑铭、写本资料贯通,则会少走弯路,如敦煌文书中不乏包含“鼻”字的胡名,如《沙州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中,就有安薄鼻、康薄鼻、贺薄鼻、石忿鼻(2次)、安数鼻,同卷失名某乡有贺胡鼻。这些“鼻”字的释读向无异议。参籍帐研究271~277页。
(24) “量”字的读法实际是对张维录文的误会。张氏因不识此字,慎重做了隶定照描,并不是用铅排的“量”字。
(25) 姜伯勤先生在《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一文中,曾据“莫覃”立论,认为“莫覃”即是见于中古汉文史料的萨珊波斯职官名“摸胡坛”,见《华学》第3辑,1998年,293页。《武威金石录》62页亦作“莫覃”。
(26) 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94、456页。
(27) 吉田丰『ソゲド语の人名再构する』、第69页。另参见[日]吉田丰:《汉字拼写的粟特人名、重构的粟特文发音及其原意》,附载于韩森《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中华书局,2004年,127页。
(28) 夏鼐:《〈陇右金石录〉补正》,初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后收入《夏鼐文集》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60~161页。
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罗丰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