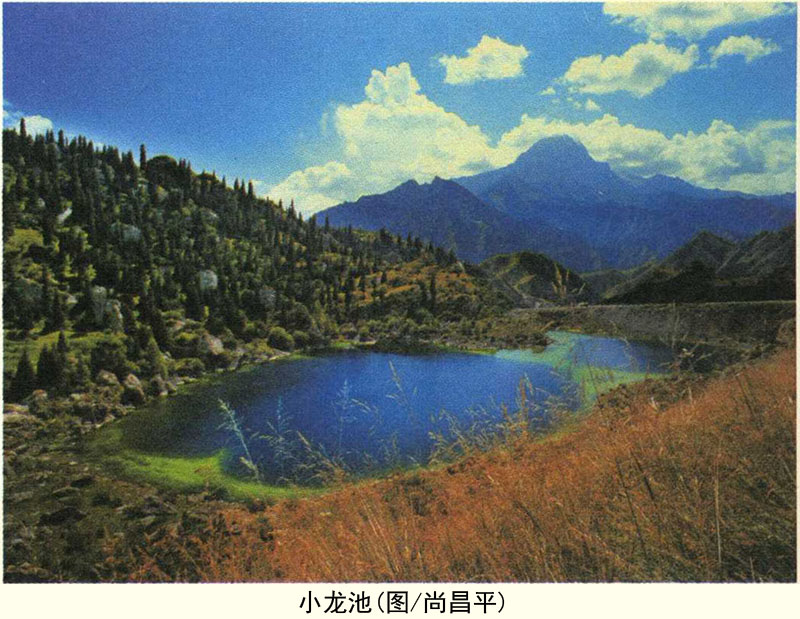在龟兹,奉佛教为国教,可谓高僧辈出,大师云集,产生了许多对佛教东传甚至中国佛教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一)白延
龟兹归慈王世子,通汉语、梵语、本民族语,为佛教东传的先驱,于曹魏时(公元254—260年)至内地,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在洛阳白马寺译出《首楞严经》2卷、《须赖经》1卷、《上金刚首经》。
(二)尸梨密
诸史籍仅谓其西域人,但不确指是龟兹,唯梁宝唱《名僧传抄》言其姓白,故近人多谓其龟兹人。相传,其本为龟兹王子,依例当为国王,后让王位于其弟,出家为僧,于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到中原,栖止于建初寺。由于其在西域地位较高,故其一入中原便得到西晋封建上层重视,丞相王导、太尉庾元水、光禄卿周伯仁、太常谢幼屿、尚书令卞望之、大将军王处冲、仆射周凯等皆为其好友。当时中原无咒法,尸梨密遂于晋元帝年间(公元318—322年)译出《大孔雀王神咒》一卷、《孔雀王杂神咒》一卷,从此中土有了咒法流布。
(三)鸠摩罗什
我国东晋时期后秦著名佛学家、佛教翻译家和文化大师,对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1.出身名门
据《历代三宝记》《佛祖通载》等佛教典籍记载:“其父鸠摩炎,天竺人也。家世国相,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
鸠摩罗什的母亲耆婆,是龟兹王白纯的妹妹,贤淑聪慧,博览经史,笃信佛法,坚韧有志,起初她要出家,其夫未许,后因出城游览,看到冢墓枯骨,异处纵横,于是深怀苦本,决誓出家,若不落发,不咽饭食。至六日夜,气力绵乏,夫乃惧而许之。剃发后仍不饮食,次日受戒。
2.随母出家
鸠摩罗什7岁随母出家,师从高僧佛图舌弥受经。“日诵千偈,每偈有三十二字,共三万二千字。”9岁,随母往罽宾国求学。
3.师从高僧
罽宾王的从弟槃头达多是著名的高僧,“明博识,独步当时,三藏九部,莫不该博,从旦至中,手写千偈,从中至暮,亦诵千偈,名播诸国,远近师之”。鸠摩罗什拜槃头达多为师。“从受《杂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等小乘佛学经典,凡四百万言,师受其义,即自通达。”鸠摩罗什以非凡的领悟力受到赞誉。罽宾王请鸠摩罗什入宫,与外道辩论,大获全胜。从此“王益敬异,每日供给鹅腊一双,粳米面各三斗,酥六合。此外国之上供也。所住僧寺,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扫洒,有若弟子。”
4.初涉疏勒
鸠摩罗什12岁时,随母归国,经月氏支北山,进入疏勒,师从来此的罽宾国小乘高僧佛陀耶舍主修小乘,时而传授大乘学说,后由沙门喜见向疏勒王推荐,升座宣讲《转法轮经》,龟兹王闻之,遣使酬谢,以示友好。
鸠摩罗什在疏勒师从须利耶苏摩,学习大乘佛教经典,他原先学过《阿毗昙》,已经接受了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的理论。后来他又游学莎车,在莎车继续师从须利耶苏摩学习大乘学说。经过这段学习,鸠摩罗什头脑中加深了对小乘佛教的怀疑,逐渐倾向大乘学说。经过反复辩难,鸠摩罗什终于放弃了小乘立场,改务大乘,并感叹曰:“我过去学习小乘,恰如有人不识真金,反把鍮石看成珍宝。”此后他又学习印度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著作《中论》、《百论》、《十二门》等,更加稳固了他改宗大乘佛教的立场,体现了他学术上的批判精神。
5.改宗大乘
关于鸠摩罗什改宗大乘之举,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在受戒前,由于不断接触大乘经论,他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他博览外道,行为也不规范,可见已有背离小乘之端倪。受戒之后,他重新游学于疏勒、莎车等国,在佛陀耶舍、须利耶苏摩等高僧影响下,终于完成了由小乘改宗大乘的哲学思想变化。当然,这个转化有一个过程。由于龟兹周围国家社会、历史的变化,大乘佛教声势日高,鸠摩罗什的思想中出现了和传统小乘之间的矛盾。他一方面博学“外道经书”,一方面接受大乘高僧思想理论,不断徘徊于大、小乘之间,不拘旧论,往复研究,方知理有所归,最后才完成改宗。
6.温宿论战
鸠摩罗什经过温宿国时,遇到一位道士,神辩英秀,名震诸国。他手击王鼓,相约论战,并扬言:“论胜我者,斩首谢之。”鸠摩罗什即以无畏的学术勇气与他辩论,使道士“即迷闷自失,稽首皈依”。鸠摩罗什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诸国皆聘以重器。龟兹国王亲至温宿,将鸠摩罗什迎回国内”。
7.名震西域
鸠摩罗什以其佛教经典烂熟于心之智,唇枪舌剑善于雄辩之才,大力弘扬大乘空宗理论,“推辩诸法,皆空无我,分别阴界,假名非实”。他20岁时在王宫受戒,初住新寺(王新大寺),后住雀离大寺,跟高僧卑摩罗叉学习《十诵律》,并广宣大乘,一时间大乘学说在龟兹蓬勃兴起。“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疑非凡夫”,对鸠摩罗什“咸推而几敬之,莫敢居上”。龟兹王特意“造金狮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鸠摩罗什由此成为博古通今、声震东方的龟兹名僧,每年升座说经之际,“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
大乘的基本特征是力图参与和干预社会世俗生活,要求深入众生,普度众生,把“权宜”“方便”提到与教义原则并重的地位。因此它的适应力强,传播渠道多,内容广泛复杂。凡它所到之地,无不带上当地民族特点。鸠摩罗什之所以改宗,主要是折服于大乘的学说,同时大乘理论与他自信开阔的性情相吻合,体现了鸠摩罗什与佛教文化合理的双向选择。
龟兹是小乘佛教的国度。鸠摩罗什是龟兹大乘佛教最初的传播者和推行者,他以对佛教经典的熟知和令人折服的雄辩口才,大力弘扬大乘,贬低小乘,使大乘一度在龟兹占优势地位。但小乘佛教在龟兹毕竟渊源久远,根深蒂固,暗中与大乘对峙着。当鸠摩罗什离开后,大乘佛教在龟兹迅速衰落,小乘佛教在龟兹重又兴盛起来了。
8.羁留凉州
前秦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中原僧人僧纯、昙充游学龟兹回归长安,称述龟兹佛教盛况,谈到该国的王新寺有鸠摩罗什,才智过人,弘扬大乘经论,名震西域。其时中原名僧释氏道安在长安,听到鸠摩罗什声誉,就意在劝苻坚迎他来长安。此后,西域鄯善王、车师前部王、康居、于阗及海东共62国的国王到长安进贡,鄯善王、车师前部王请求苻坚西征,并“请为向导”。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坚派吕光任都督率兵七万西进,并对吕光说:“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则驰驿送什。”建元二十年,吕光攻陷龟兹,废龟兹王白纯,立其弟白震为王。吕光获鸠摩罗什后,并不速送入关。因吕光原不奉佛,莫测鸠摩罗什智量,又见他未达高年,便以常人对待。还强迫鸠摩罗什破戒,与龟兹王女结婚。鸠摩罗什拒而不从,吕光说:“道士之操,不愈先父,何所固辞?”于是“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吕光还时常让鸠摩罗什骑牛和劣马,伺其坠地而戏弄他。
次年,吕光带着鸠摩罗什在归军途中到达凉州,得知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打败继而被部属姚苌所杀,于是割据凉州为王,建立后凉政权,建都姑藏(今甘肃武威)。如此,鸠摩罗什也就在凉州滞留下来。
鸠摩罗什在凉州17年,吕光只把他当做能占卜吉凶、预测祸福的方士。对于佛法,“吕光父子既不弘道”,鸠摩罗什便只能“蕴其深解,无所宣化”。
鸠摩罗什在凉州17年,虽然没有从事译经传道活动,但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钻研了汉语,大量接触佛学以外的汉文经史典籍,成为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饱学之士。他在对东西方文化的精细考辨和对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会贯通过程中,深化了自己的文化哲学思想,从而确立了他贯穿着世界视野、创造精神和佛教中国化的独特文化观。
9.译经长安
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原前秦将领羌人姚苌在渭北建立后秦政权,自称万年秦王,两年后,称帝于长安,国号大秦。他听说鸠摩罗什之名,曾虚心邀请,但后凉吕氏认为鸠摩罗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拒绝放行。后秦建初九年(公元394年),姚兴即位后,又遣使邀请,后凉仍未放行。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陇西公姚硕德西征,后凉王吕隆大败而降,鸠摩罗什这才被后秦迎往长安,时年已58岁。
当时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原和西域各城邦之国的主流文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非常需要借助宗教的威力。因此,中原王朝高度重视佛教僧侣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同时,鸠摩罗什精通佛法,早在西域已有盛名,深受统治阶级的器重和佛众的仰慕,已成为当时佛教文化的一位杰出代表、西域和中原文化交流的一位伟大使者。
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姚兴待之以国师之礼。宗室显贵都信奉佛法,公卿以下莫不归心,长安上下名僧云集,法化颇盛。鸠摩罗什的到来适逢其时,如鱼得水。弘始四年(公元402年),鸠摩罗什应后秦姚兴之请,住逍遥园西明阁译经。他收弟子八百,率领僧众三千,开始从事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译经活动。这次译著佛典,工程浩繁,数量惊人。鸠摩罗什主译的主要经典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十诵律》等,共74部,392卷,第一次系统而正确地向中原介绍了大乘空宗理论。
鸠摩罗什译经庄重严谨,常“一言三复”“与众详究”,因此他的译文“意皆通圆”“词润珠玉”,弟子们称誉“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在翻译文体上,鸠摩罗什一变过去拙朴古风,开始运用达意译法,使诵习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特别是传译具有文学趣味的大乘佛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等时,力求不失原意,重视表现原文语趣,表现了鸠摩罗什高度的责任感和高超的文学鉴赏力、表现力。由于他学贯东西,精通胡汉,因此他能“手执胡经,译秦言”,但他的译文则坚持“曲从方言,趣不乖本”的原则。他还根据中原诵习者的特点和需要,在传译中或增或删,务必文顺意达,使佛经语言中国化,成为中国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鸠摩罗什在凉州生活17年,早已了解内地佛教传播情况和前代译经的优劣处,因而他的译文含义准确,简练精辟,词语通达,文笔流畅,使原著思想内容更加清晰明朗。所以他的译本比其他译本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在我国翻译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
鸠摩罗什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和中原以往的译经基础以及当时长安译场的许多得力助手分不开。后秦译经事业,基本上继承了前秦时道安所创的旧规。由于后秦朝廷及国主全力支持,才使小型译坊扩展为国家译场。是时势造就了大翻译家鸠摩罗什。
1O.佛学哲理
鸠摩罗什在译经的同时,从未放弃过登坛讲经,弘宣其佛教哲学思想。他用独特的思辨方式,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实质概括为“一无常、二苦、三空,四无我”,把现实世界看成是无常、虚幻,人的主观世界也是虚幻,只有佛教的极乐世界才是真实存在。为了达到从根本上否定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引导人们皈依大乘佛教,鸠摩罗什就大力推行“中观”的手法,这是富于诡辩性和欺骗性质的方法论。“中观”的手法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直接说客观世界不存在,也不说它是绝对虚无,而是把它看成“假有”,是虚假的幻象。既然是“假有”,当然便不能再说是绝对虚无,对这种说法,身临现世社会生活的人们容易解除思想警戒而乐于接受。殷鼎先生在论鸠摩罗什时指出,当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坚持客观世界的精神主体说时,各执“有”和“无”,而“有”和“无”正是魏晋时期主要思想流派之间僵持不下的哲学课题;鸠摩罗什则另辟蹊径,貌似公允地来了个“有无双道,不落两边”,既不说有也不说无,而把客观世界说成“非有非无”,并用水中月来比喻世界只不过是个幻影,认为世界既不是真实存在,又不是绝对虚无,最终认识到现实世界是死寂相,是一切皆虚妄,这才是他哲学思想的真谛。从而引导人们把彼岸的涅槃及其绝对精神看做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人的主观世界虚妄论”,这是鸠摩罗什给中国唯心主义哲学输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鲜命题。这种别开洞天的辩术充分显示了鸠摩罗什大乘哲学的独创性和思想智慧的锋芒。
鸠摩罗什虽然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主要是传播大乘空宗思想,但在当时大多数人不懂梵语的情况下,往往把传译者看成是思想理论的创立者。因而,龟兹出生的鸠摩罗什,就起到了中国佛教理论奠基人的作用。
11.文化伟绩
鸠摩罗什的译经弘法活动,不仅对中国佛教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译著对其后散文、诗歌、戏剧、小说创作都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佛教塑像、绘画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雕塑、绘画、建筑等),是宗教宣传的载体,因此,文化各门类是服从佛教教义的。但任何文化艺术的本质都是以追求美为目的,经典教义提出抽象的题材内容,而在体现这些题材内容时,则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余地。就如鸠摩罗什,在传播佛教文化中,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一直是他治学的灵魂。他翻译的佛经有许多是文艺性很强的,既有哲理智慧,又有故事情节,在文风上冲破了六朝时士大夫阶级那种华而不实的的文风,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有些章节,从结构内容都具备了短篇小说的特点,有的偈语则显露出哲理诗的品格。这些译著,成为当时广泛流传的文学读物,并对我国文学创作和民间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
他不仅在译经中注重译文的文学色彩,而且本人也善于诗文,可惜只有两首诗作传世。如《十喻诗》:
一喻以喻空,空必待比喻。
借言以会意,意尽无会处。
既得出长罗,住此无所祝。
若能映斯照,万象无来去。
从这首宣扬佛教教义的诗中,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对汉语古诗技巧的熟练运用。另外还有一首《赠沙门法和》:
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
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常作颂赠沙门法和等,凡为十偈。可知这首赠法和诗也是偈语。意在称颂法和译经工作意义重大,可以培育美德,流传天下,将法和之译作比为“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从《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之《全晋诗》卷七仅收的这两首诗,就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古体诗创作的功力。
鸠摩罗什翻译的数百卷经典,极大地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发展。风行各地的佛寺、佛塔,形成了中国建筑的独特格局,成为影响后世建筑的坚实基础。遍及全国的石窟寺塑像和壁画,为汉文化的心理结构和民族精神注入的新鲜血液,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开凿石窟,是佛教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产物。石窟寺是安置佛像的殿堂,寺内壁画是宣扬佛教的形象教材。这里描绘的就是经典中天国乐土的缩影。在这种建筑主题的要求下,绘画雕塑和图案装饰把洞窟渲染成五彩缤纷、灿烂瑰丽的佛教净土、理想天国。于是洞中的主体塑像就在这样庄严肃穆而又温暖宁静的气氛中接受僧众信徒的顶礼膜拜。但是,这些佛教艺术的真正创造者,是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他们的创造虽然是佛教艺术,但也带着艺术家鲜明的审美个性,因此,石窟寺塑像、壁画就不仅是对教义的宣传和对佛陀的崇拜,同时也是艺术家对真、善、美的追求,是艺术家的审美创造。宗教可以消亡,但艺术是永生的。
鸠摩罗什所处的时代,正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从西域到中原,寺院林立,戒律森严,像鸠摩罗什这样的高僧大德不断涌现,大大促进了各地建造石窟、塑像和创作绘画的速度。当然,对其故乡龟兹的佛教艺术更会产生重大影响。他在龟兹先循小乘,后奉大乘,大乘因此在龟兹盛行。从克孜尔千佛洞中大佛窟可见其影响,大立佛高达15米以上,没有他这样的高僧倡导是很难建成的。47号窟也有大型佛涅槃像,在佛的头光和身光光环中,绘有不少小立佛,这种形式与小乘涅槃形式不同,是受鸠摩罗什弘扬的大乘佛教影响所致。当时,鸠摩罗什在龟兹传播佛教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石窟寺壁画中都有反映,如佛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成为壁画创作的主要题材,绘画风格也因为高僧大德皆为西域人而呈现出本地民族特色,人物造型具有龟兹人的特征。
特别是到长安以后,后秦国主姚兴的佛学思想受到鸠摩罗什的直接影响,甚至可以说姚兴的佛教观就是鸠摩罗什的佛教观。由此可见,其佛教思想波及到后秦统治的广大地区。在麦积山石窟寺早期塑像中,就可以看到以三世佛为题材的塑像。秦陇地区的石窟寺中出现大量“维摩诘”“阿弥陀佛”及“维摩诘经变图”“阿弥陀经变图”,这与鸠摩罗什较早在后秦传译《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并广泛弘扬有关。炳灵寺169号窟中有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维摩诘经变图》《西方净土变》和西魏时的《维摩诘文殊辩法》等壁画,麦积山127号窟《西方净土变》壁画中绘有飞天乐舞伎人物形象,手持龟兹乐器多种,这可能与来自龟兹的译经人鸠摩罗什不无关系。
另外,凉州石窟寺的开凿,也使人联想到久居凉州的鸠摩罗什。后秦时鸠摩罗什在天水武山水帘洞建过梵宫僧舍,使“捎拉寺”声名远播。据记载,“捎拉寺”是在鸠摩罗什鬼斧神工所造。由此可见,鸠摩罗什在秦陇地区信徒中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
中国石窟寺的造像和壁画艺术,是佛教文化的形象资料,是佛教文化精神的生动体现。鸠摩罗什所译佛经的广泛流传,成为艺术家创造佛教艺术的文字范本和构图依据。鸠摩罗什在传播佛教方面作出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秦陇和龟兹石窟艺术的创造,而且对全国众多石窟寺艺术产生了影响。
12.不历小检
据《高僧传》载,鸠摩罗什“为性率达,不历小检”,到长安后又娶宫女为妻,生子二人,并受使女十人,不住僧舍,别立解舍,供给丰盈。这与佛教的戒律与所传的教义相违。但是鸠摩罗什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每至讲说,常先自嘲:“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也,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
13.一代宗师
作为一代文化大师的鸠摩罗什,其文化观的真正确立,则是在被吕光带到凉州的17年中。经过广泛研读佛教经典,他成为中国佛教学派建立自己宗派哲学理论基础的第一人,他所阐发和建立的佛教文化观,也同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可以说他在后秦开一代佛教文化之风,使凝滞纷乱的中国佛教学术思想因他而面目一新。
鸠摩罗什最后——也是最辉煌的十几年,是在长安度过的。经过凉州17年的磨炼与积累,到长安后他才思迸发,大显身手,弘扬佛法,广出妙典,使“法鼓重振与阎浮,梵轮再传于天北”。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述,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照本来面目介绍到中国,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兴盛和以后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起到首开先河的作用,其影响波及到他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同时他还以诗化的笔触、细腻的情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他翻译的佛教经典更具文化个性和中国特色,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佛教文学创作和造像绘画艺术中,鸠摩罗什的译著和文化观,被作为一种精神依据和形式规范,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发挥着作用。
(四)佛图舌弥
佛教传入龟兹后,最早盛行的是小乘佛教,佛图舌弥是公元4世纪中叶龟兹最有造诣的小乘高僧。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称:“僧纯,昙充拘夷国来,从云慕蓝寺于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比丘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剑慕法。”在此书《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还列出了佛图舌弥所管辖的寺院。属于比丘的寺则有“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属于比丘尼的寺院则有“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再加上为僧纯、昙充受比丘尼戒本及戒法的云慕蓝寺,共有八寺之多,可见佛图舌弥在龟兹佛教界地位之高,势力之大,在文中还特别指出罗什出家后,曾师事佛图舌弥,并说佛图舌弥所辖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族妇女,为道远集斯寺”。可知他在小乘学方面的造诣已誉满西域,实执小乘学萨婆多部的牛耳。
(五)木叉毱多
木叉毱多,是隋末唐初龟兹小乘教高僧,声望颇隆。年轻时曾往印度学习佛教诸经20余年。回龟兹后,即住于阿奢理贰大寺,宣扬小乘佛教,被龟兹王及人民尊为大德高僧,当时汉地佛教高僧玄奘是大乘教徒,唐初所以要西去印度学习,目的是要学习大乘有宗最重要的《瑜伽师地论》经典,想寻求解答凡人通过什么阶段和什么手续才能成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玄奘西行时,木叉毱多已年迈,但闻玄奘至,仍赶往龟兹王城,和王、众大臣、群僧迎迓东门外。
(六)达磨笈多
南印度人,属刹帝利种姓,25岁受戒,曾遍历印度各国及主要寺院。后闻东方有佛教大国,佛法颇隆,即从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境内)东越葱岭经疏勒,约于公元585年至龟兹,停住王寺两年,一面学习东方语言,一面为众僧讲解《释前论》《如实论》。因当时龟兹王笃好大乘,听其宣讲后,开悟颇多,为此每讲必到,旦夕相伴。坚欲留他长住。可是达磨笈多东来的目的是要到中国中原去。由是两年后,只好密偕一僧潜离龟兹,间道经过焉耆、高昌、伊吾东行,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冬十月至洛阳,专力译经,在28年中共译佛经7部31卷,其中较有名的有《摄大乘》《药师本愿》。
(七)佛陀耶舍
罽宾人,13岁出家,27岁受戒;佛学造诣较深,在社会颇有名气。为了弘扬佛学,即至疏勒,受到疏勒王太子达摩弗多的礼遇和供养。罗什从罽宾返回龟兹途中,路经疏勒,慕其名,即向其学《阿毗昙》《十诵律》,罗什返回龟兹后不久,达摩弗多承袭疏勒王位,曾一度出兵增援龟兹抗击吕光军。在他出兵出外期间,即命佛陀耶舍辅佐太子执政。十多年后,达摩弗多王死后,即前往龟兹宣扬佛学,由于他学识渊博,受到众僧敬重,被奉为龟兹高僧。已经东去姑藏(即凉州)的罗什,闻佛陀耶舍在龟兹宣教,即去信劝其东去。佛陀耶舍正整装东行时,龟兹众僧群起挽留,只好暂缓起程。一年后,佛陀耶舍又率弟子密起行装,潜离龟兹。他先至姑藏找罗什,哪知扑了个空,又赶至长安,才找到罗什,即住在逍遥园,与罗什共译《十住经》,同时传授《昙无德律》《长阿含经》。罗什死后,又返回罽宾,但对中国佛教的弘扬,仍系念于怀,因而寻得《虚空藏经》一卷后,仍千方百计托商贾带往凉州。
在东汉末、魏晋时期,高级僧侣都离开龟兹去国外的索格底亚那(河中)、巴克特利亚学习。那时正是大月氏国贵霜王朝大力弘扬佛教时期,因而大月氏国、康居国高僧辈出,龟兹的早期佛教实际上是由大月氏国、康居国传入。所以早期龟兹高僧都前往学习。后来罽宾国已经发展为印度小乘教中心地,而龟兹也以小乘教一切有部为主,因而东晋十六国时期龟兹小乘高僧都前往罽宾留学,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即是。同时罽宾的不少小乘教高僧也不断来到龟兹弘扬小乘教,如盘头达多、佛陀耶舍、昙摩密多、卑摩密多等。
随着大乘教在印度隆兴,中原的大乘教高僧不断西行去印度学习,如法显、宋云、惠生、玄奘、慧超、悟空等都先后西行去印度求取大乘佛经及律藏、经典。而中国中原大乘教各宗派兴起后,印度一些高僧又慕名前来龟兹及中原各地留学和宣教,如阿质达霰、达磨战捏罗、昙无忏等。
通过对一些高僧的叙述,可知龟兹佛教的发展过程:最初以小乘为主;鸠摩罗什前后,即公元4世纪时则大小乘并举;南北朝时期,即公元5—6世纪时以小乘教为主,大乘教也有一定势力,并兼有禅、密宗流布;隋唐时期,龟兹僧侣几乎全是小乘教,只有汉僧行大乘法。
由于小乘教提倡个人苦修,所以龟兹僧侣必须按照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十诵律》出家修行,僧侣每三月需易寺屋,初出家者不准独自住宿。比丘尼也是三月一易寺屋,需三大尼才可以出行。每个人初入佛门,需跟随本师学习佛教基本常识,背诵入门要籍数十万言的经、律、论佛经,才能剃度,成为僧侣,然后才准告别本师,离开本寺到外地游学,弘扬佛法。许多葱岭以东妇女不畏远道,长途跋涉来龟兹,削发为尼,修习佛教,可见当时龟兹在西域佛教界的地位。
龟兹佛教所以特别发达,是与王室贵族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当时在王宫中雕镂佛像、彩饰严装,与寺院无异。同时龟兹国王还常往著名寺院礼佛供养,对一些有突出成就的高僧还待以殊礼;还在龟兹西门外,建造高九十余尺的大佛像,“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甚至重大政治、军事大事也都和高僧共同商决。对此,玄奘特别指出,龟兹国“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足见龟兹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而自公元3世纪起佛教在龟兹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后,不断有王室贵族剃度出家,成为高级僧侣,如在魏晋期间前往中原的高僧曾有白延、帛尸梨密多罗等。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文化史,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震荡是十分剧烈的。包容的中华民族接受了外来的佛教文化,但同时也开始了对佛教的消解、融合、改造和重建的过程,使佛教文化中国化。站在中华和西域文化前沿的龟兹古国,把民族自信当做自己的重心,凭借非凡的魄力与胆识,在动人心魄的乐舞声中,张开双臂拥抱外来文化,同时施惠天下,让丝绸之路大放异彩,使佛教艺术走向高峰。
丝绸之路敦煌研究/王功恪,王建林编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