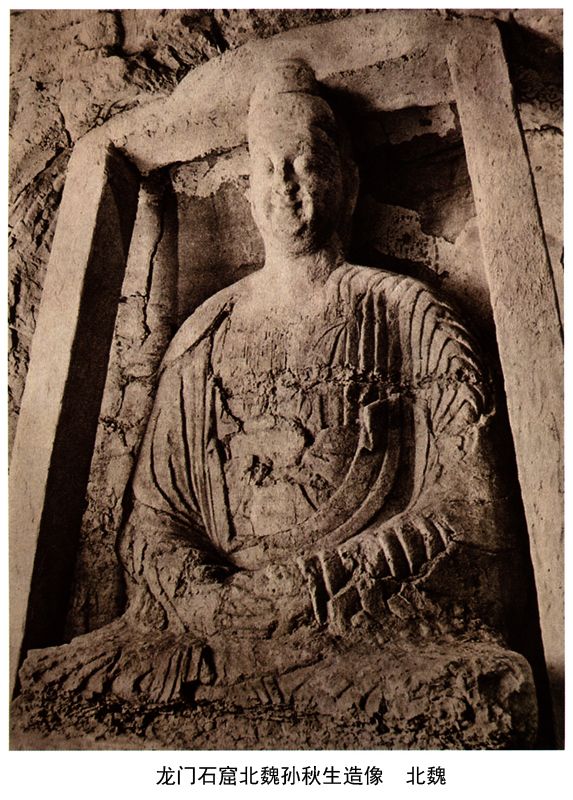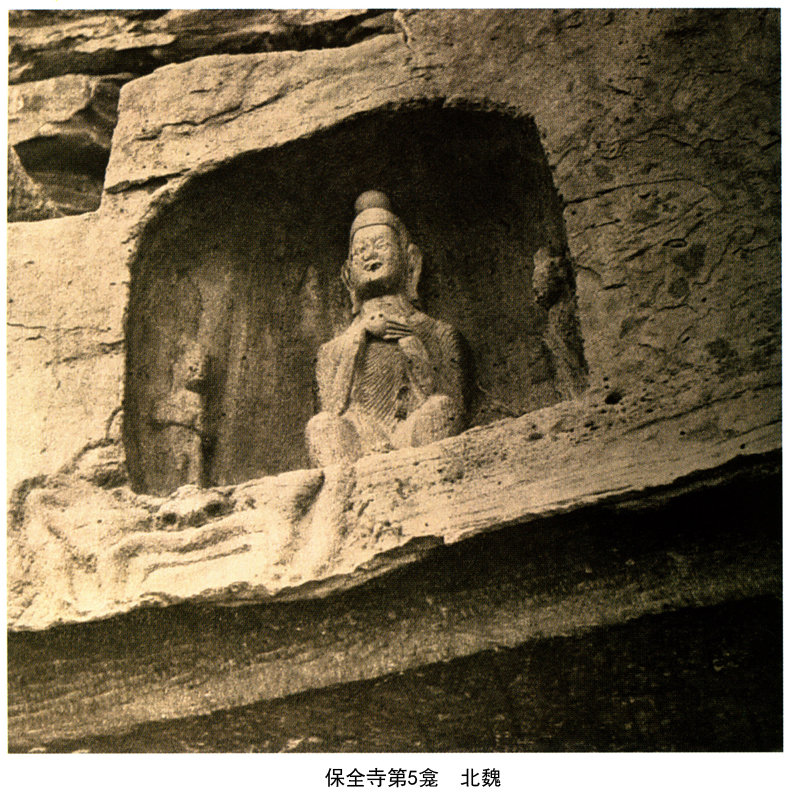“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使惹尘埃。”六祖惠能偈曰:万物皆空灵,空灵即是佛。而敦煌成不了佛,因为在敦煌的历史上沉积了太多,难以空灵,难以超脱。一个多世纪以来,朝拜者往来不绝,将敦煌奉为信仰,心甘情愿地拜倒在佛龛下、洞窟中,非为向佛,意在敦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敦煌尘缘未了,继续以其独特的风姿伫立尘世间,将历史凝固,迎接更多的善男信女,穿越时光隧道,在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忆中拥抱敦煌,而后回到未来,圆了自己的“敦煌梦”,作为“寻梦人”,却情愿长梦不醒,情愿在敦煌的历史中沉醉自己。
(一)
大约在公元2世纪前后,作为文化重镇的敦煌就显示出凉州文化的独特魅力。书法家张芝、索靖,经学大师敦瑀、宋纤、刘昞,医学家张存,音乐家索丞等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名人(《太平御览》)。有史为证,西凉时期敦煌地区就建有国王李皓的“靖恭堂”、“谦德堂”、“嘉纳堂”等著名宫殿。宫殿里绘有大量壁画,虽然现在无法考评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但能在这边远的西北一隅如此隆重地图绘建筑壁画,足可见其文化底蕴之深厚,全不像正史中所谓少数民族只知“游牧射猎,远离教化”的记载。
敦煌地区3~4世纪艺术珍品的遗存,已初露其独特文化的魅力:敦煌佛爷庙晋墓出土的墓砖画、酒泉丁家闸墓出土的墓砖画、嘉峪关墓出土的墓砖画……既反映了河西地区历史社会风貌,同时在造型上和艺术处理上显现出其不同寻常的水准。由此可见,在敦煌石窟艺术辉煌之前,汉晋文化传统便形成了极为深厚的基础。它以一种接纳的态势迎接和主导着未来敦煌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
佛教艺术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之后,敦煌文化产生了新的转变,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其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崇高地位才逐渐彰显出来。
据史苇湘先生考证,早在两汉三国时期,敦煌就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西方商队和使节东进,同时也伴随着佛教的东进。汉晋简牍中就记载了敦煌地区的“过所”,说明这里在当时就有僧徒们活动的庙宇。随着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大约到了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禅定影响到了这一地区。禅定是佛教徒通过精神集中、观想特定对象而获得佛教悟解或功德的一种修习活动,相比较于早期的译经、讲经,修习禅定更需要安静的环境。因此,开窟建寺、设置修习场所乃成盛事。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很可能就有这一原因的驱动。
敦煌莫高窟的正式开凿却完全出于偶然,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366年,有个名叫乐僔的敦煌禅僧,在城郊散步时到了莫高窟附近,忽见山上一派金光,似乎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显现。他被这奇景眩惑,认为这里是圣地,于是募人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石窟。其实,乐僔所见的金光与千佛,应和海市蜃楼一样,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现象。乐僔是严守戒律、离世脱俗的禅僧,所以,他所见的海市蜃楼也就充满了其所追求的佛教色彩。乐僔开窟后不久,又有个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西行到敦煌,在乐僔所开石窟的旁边又开了一窟。
偶然的邂逅竟有了文化艺术的神奇,366年莫高窟开始修建佛教石窟,历经1600余年的风霜雨雪,敦煌地区的佛教艺术以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为中心的众多石窟寺共同构成了敦煌艺术的极致,佛教文化艺术开始在这里扎下了根。
4世纪开始,随着敦煌地区石窟的开凿,敦煌历史文化的意义更多地与佛教艺术链接起来。在此后1600余年的历程中,敦煌地区的文化因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石窟艺术而共同构成一条连贯不息的历史长河。
(二)
4~6世纪,敦煌经历了十六国、北魏至北周、北朝时期的历史演变,其佛教艺术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西凉—北凉时期的石窟造像,更多西域之风,其内容因敦煌民众不堪战祸、熬盼“弥勒下生”的愿望,而多为弥勒菩萨、禅宗佛和说法佛。从弥勒那沉思俯视、垂悯下界的神情与举止,佛国世界显然更多了些众生的企盼。值得注意的是,洞窟内除了塑像外,四壁及天顶画满了壁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图像世界。人们走进洞窟,就犹如走进了佛国天界。与其说这是对观赏者在进行美的熏陶,还不如说它是在引导教徒们从内心深处来信奉佛教。
北魏时期,敦煌地区的佛事异常繁盛。516年北魏易敦煌为瓜州,该地成为东西交通的主要驿站。元魏宗室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因其佞佛,使得敦煌窟寺不断增多,并且留下几百卷藏经写本。到了北周宇文氏统治时期,尊经重儒,敦煌北周的15个洞窟反映了这一时期在创作内容和艺术技巧上的进步,为隋代石窟艺术丰富的表达能力起到了续接和筑基作用。这一时期,东西交通极为顺畅。北周壁画《善子太子入海缘品》和《福田经变》中那繁忙而成群的商队,使我们又隐隐听到了历史带给我们的驼铃之声。
从366年到580年的二百多年间,因为有着中国汉晋文化传统的基础,敦煌石窟艺术始终都在固执地遵循着外来佛教仪轨,却也无法避免被悄悄地汉化了。作为外来的宗教艺术,要想在具有发达汉文化的敦煌扎根生长,获得当地民众的青睐,就必须在题材内容、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和当地思想文化协调一致,以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是表现形式上,其转变历程在壁画和塑像中清晰可见(虽然这种迹象不如后来明显),比如,在西域还相当流行的印度式“丰乳细腰大臀”的裸女和菩萨,当她们风尘仆仆地来到敦煌时,由于大家都在“非礼勿视”,便只好含羞地躲了起来,代之以“非男非女”的菩萨、飞天和伎乐了——这便是最典型的佛教艺术中国化。
(三)
580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了隋朝。隋朝虽因炀帝的荒淫无道成为短命王朝,却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隋朝南北的统一,加上又是个极信佛教的时代,于是南北佛教艺术获得了空前的交流,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也更为畅通,敦煌圣地成了过往商旅布施祈祷的重要处所。仅隋代短短的37年间,就留下了79窟之多。
隋朝敦煌的佛教艺术发展十分迅速,石窟艺术汉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虽然早期北朝风格占有统治地位,但不久便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佛与菩萨造像不再是秀骨清像式的苦修之士,大多广额丰颐、体态健硕,俨然暗示着这些净土中人也来自民众凡俗。这正折射了隋代人希望来自西土的圣神、大慈大悲的“济度者”,真正能济度人间忧苦的心态。这种形态递变和意趣上的转变,使得佛教艺术更多了艺术审美的诱惑和情感魅力。
(四)
大唐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的三百年,也是敦煌石窟艺术最为辉煌的三百年。初唐的石窟艺术,虽然因为战乱仍未脱离隋代末年的风格与特色,但很快,随着唐王朝统治的巩固,统治者对丝绸之路的高度重视及对佛教的佞信,敦煌石窟艺术新的气象、新的面貌不断地出现了。
按照史学界分期,唐代以755年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安史之乱给唐王朝的冲击极大,但因敦煌地处边远,并无大规模战火殃及,所以敦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786年吐蕃王国占领敦煌,却给敦煌带来了十分明显的影响,因此,敦煌学界一般以786年为界把唐代敦煌历史分为前后两期。
初唐时,敦煌仍称瓜州,属于秦王李世民总管的凉州。由于吐谷浑、突厥等势力侵扰河西,唐王朝曾一度阻止人民西行,这对敦煌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虽然不久唐朝改瓜州为沙洲,但并未能改变敦煌地区地方势力雄踞的局面。唐王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没有让这一局面持续很久,首伐高昌凯旋,使得东西沿途继续畅通;再建西州并置西域都护府,统治河西各地,使得敦煌重获稳定与发展。贞观十六年(643)在莫高窟建造的第220窟,无论是壁画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显示出唐代的面貌和水平。其中的《帝王图》,其优美的造型与绚丽的色彩,显示出精深的艺术造诣和典型的唐人风貌,似乎是佛理的图解,更是唐代人间生活与想象的写照。与前期石窟艺术相比,唐代石窟艺术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汉族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接纳、兼容与改造的特点。
进入盛唐,西部为强大的吐蕃王朝势力覆盖,武周时期双方冲突不断,敦煌地区同样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但石窟艺术并未因此而中断。或许是战争中的人们祈求着人生的平安与吉祥,或许是武则天对佛教的崇敬与佞信,佛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完全可以制造舆论为武周政权作出正面诠释,使这一不正常的变革换代合法化。千秋万世后,佛的精神永存,而一代女皇的丰功伟绩却尘封在历史中,只留下无字碑作证。
盛唐敦煌石窟艺术更加呈现出中国本土化风格。史苇湘先生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中说:敦煌从前秦建元二年建窟,佛教徒就把弥勒菩萨塑在重要的宫阙里,俯视下界芸芸众生。到了唐初把“上生”“下生”合而为一,但“弥勒下生经变”仅以儴佉王、妃、太子及诸大臣剃度为主要形式。而盛唐时期,《弥勒变》就成了包括弥勒佛与诸菩萨在内的当时“风俗画”了。正是这种“风俗画”的表现,敦煌石窟艺术以图像的形式传递着唐代的历史文化信息,并准确地保留至今。它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与考察唐代敦煌地区的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图像资料。
8世纪后期,敦煌地区成为吐蕃领地。其统治者大兴佛教,吐蕃赞普曾颁法令:一人出家调拨七户平民为寺户。这样一来大量土地属于寺院,寺院经济空前繁荣。寺院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佛教石窟艺术的振兴。这一时期,石窟壁画、塑像制作精致、细腻,笔墨精湛,线描造型准确生动,比盛唐多有发展,是唐代敦煌艺术向深度拓展所取得的成就。
寺院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敦煌文化的异常发达,所不同的是,这一文化的传承更多借助于寺院的和尚教师。而且,虽然唐与吐蕃存在多次战争与纷争,但宗教与文化上的联系从未间断,两地僧侣往来频繁,这就决定文化传播的内容不仅限于佛经,中国传统的经史和内地流行的名篇,都是敦煌学子们接受的最好典范。吐蕃统治时期的张议潮正是在这一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位汉唐子孙后来能够归依唐朝,不能不说明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内驱力在发挥作用。
张议潮收复沙州、瓜州共十一州之后,晋献给李唐王朝,唐朝便于847年设此十一州节度使于沙州,张议潮理所当然为节度使,后改号为归义军节度使,自此河西地区进入了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代。归义军统领期间,前期为张氏集团,后期为曹议金世家执政,张、曹两家世守瓜、沙,建下了不朽功业,尤其对保证西域交通的畅通,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交往,扩大贸易,繁荣经济以及西域风俗的融会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但就石窟艺术而言,除了后期曹氏曾对敦煌石窟作过整修以外,在造像内容与风格上并未突破吐蕃时期,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
1036年,党项首领元昊领兵西征,一举攻陷肃、瓜、沙三州。从此,西夏占有河西地区,其统治也近二百年。虽然这一时期又为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割据性政权,但瓜州一带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所发展,并保持了与中原相一致的水平。西夏时期,敦煌石窟艺术也有建树,仅莫高窟就建有64个之多,榆林窟中西夏时所建之窟,多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点,形成自己文化特性:它既有北宋的笔墨构图、辽金的造型和纹饰,又有吐蕃的佛教题材和回鹘的服饰,但最终仍突出自己民族的特色。
(六)
1226年,蒙古铁骑攻占沙州,敦煌归入蒙古帝国版图,成为跋都大王的封地。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于1277年把敦煌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并在此重新设置沙州。当时,沙州除蒙古族、汉人以外,还有更多的回鹘人从事农商,吐蕃人从事畜牧,西方的波斯、大食、印度等国的使节、僧侣、商团等也有取道敦煌而达内地,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敦煌又一度进入文化经济的繁荣时期。但敦煌的地位此时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汉唐时,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而此时它虽也为重要的通道,但中亚至蒙古的草原之路被频繁使用,就使得敦煌失去了原有的交通地位;其二,元期疆域广大,敦煌虽为西北重镇,但作用已不如以前,而且蒙古军也不像汉唐时屯驻敦煌,而多屯驻敦煌东一千多里的沙州,敦煌成了边防线之外的城镇,只有部分汉军戍守;其三,蒙古都城前定和林,后为大都,与唐宋时期相比,都城与敦煌相距更远,因而敦煌的战略地位必然随之下降。由于元朝统治者也笃信佛教,这对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与发展还是有利的,元朝莫高窟虽仅存9窟,榆林窟仅存6窟,但制作精良,艺术性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元代还在瓜、沙地区建立了许多寺院,这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随着大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敦煌一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为缓慢。加上人为的不重视,造成肆虐的风沙像势利小人一样蚕蚀着被冷落的佛像,只余下结网的蜘蛛在锲而不舍地维护着信徒们的尊严,使得敦煌几乎被世人遗忘。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重新显露出敦煌文化的巨大财富,敦煌自此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解放后,新中国对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与研究,使得这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莫高窟第254窟 西域妆饰女 北魏
●莫高窟第254窟,修建于北魏,隋代重修。洞窟形制为: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棋顶,有中心塔柱。此图名“西域状饰女”,反映了莫高窟早期石窟的西域之风。这浓状的对面两女子,其面部表情,于静穆之中透露的仍然是非人间的佛国温情。
莫高窟第419窟 萨埵本生 隋
●本生故事是宣扬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救世救人的善行。此为萨埵本生故事,画萨埵王子为救老虎而投身跳崖的情节。故事曲折生动,突出地表现了萨埵舍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的决心。
莫高窟第217窟 净土变中的建筑 唐
●“净土变”包括东方净土变、西方净土变、十方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等。“净土”即佛国世界,佛经称之为“极乐国土”,那里只有幸福、美好而无痛苦、丑恶。此为莫高窟第217窟净土变中的建筑。
莫高窟第158窟 献缨络飞天 唐
●飞天也叫香音神,是乾闼婆(天歌神)、紧那罗(天乐神)的合称,她们的职能是以歌舞、散花来侍奉佛,同时能散发出奇妙的香味,是带来欢乐幸福的使者。此为莫高窟第158窟“献缨络飞天”壁画,造型极为生动,那自由飞翔的飞天,真有“天衣飘扬,满壁生动”的效果。
莫高窟 观音菩萨立像(木制彩色) 唐
●敦煌石窟中的木雕是敦煌艺术中数量较少但极有价值的文物。这尊木雕因两臂残失而较难明辨人物身份。但从其头部残缺处留下的痕迹看,在她的头部上端应当还有个宝冠,另有可能为多臂之像,这尊木雕当为菩萨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