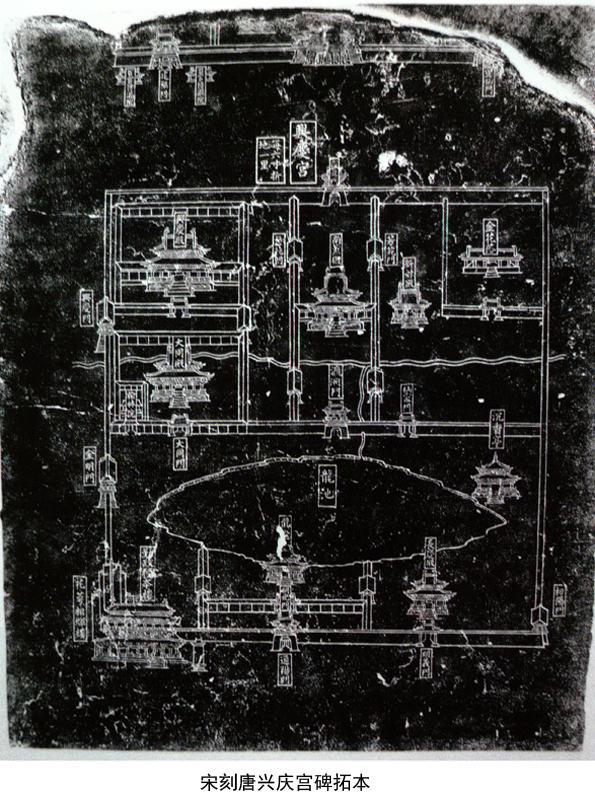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邺城”已经是十分遥远的名词了。
当大漠荒野之中的塞上平城吹响迁都洛阳的苍凉胡笳的时候,当故都洛阳的伊水之滨凿窟礼佛的弥天狂潮甚嚣尘上之际,位于漳水之滨的“邺城”还只是一个萧瑟破败的旧都之地。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三十余年过去,一个与这座北方古城有着太多历史渊源的“六镇兵户”高欢,竟奇迹般地在鲜卑贵族的残酷争斗中脱颖而出。他以机敏狡诈的勃勃野心,逐步登上了北魏大丞相、都督中外军事、渤海王的显赫高位,也将分崩离析的北魏皇室余孽,强行胁迫到远离旧都洛阳的“邺城”。
曾经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洛阳繁华,一夜之间便化为过眼沉沙!邺城成为总领中原半壁河山将近半个世纪的赫赫皇都,成为替代旧都洛阳的又一个佛教中心。而另一个曾经是高欢显迹之地的汾水晋阳,也一跃成为足以与“上都”邺城平分秋色的“下都”之地。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太行山辚辚啸啸的车马声中,近十万故国僧侣,无数卷佛教经典,无可奈何地追随高欢铁骑的车马尘尾,跋山涉水,逶迤北上。
公元550年,不可一世的高欢次子高洋,终于撕掉温情脉脉的“辅佐”面纱,取代东魏而建立北齐。自此,黄河中下游最强大的两大军人政权割据局面遂正式宣告形成。
为了维系钢刀铁骑所换取的军人政权,北齐王朝不得不承袭北魏政权所缔造的佞佛传统,将5世纪以来中原北方的崇佛高潮更加狂热地推向极致。先是下诏设置“昭玄上统”,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师”,接着再将当时与菩提达摩所并称的僧稠禅师请至邺城,为其建立华美富丽的云门寺,同时下诏敕命其兼任北响堂一带的石窟寺主,一时朝野上下事之如圣,尊称其为“大禅师”。
帝都的易位播迁,朝廷的佞佛国策,使得北齐的伽蓝佛教空前高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武成帝河清年间(562—564),北齐境内的伽蓝寺院已经暴涨至四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余万。仅上都邺城一地,就有寺院四千多所,僧尼八万余人。至于醉心礼佛的清信士、清信女,盲目结社希冀脱离苦海的“邑义”、“邑子”,更如蚁攒聚,不胜枚举。偏居漳水之隅的北齐国都,俨然荣膺了东方佛教中心的桂冠。
从高欢控制孝武帝以作傀儡,到高洋倾覆东魏建立北齐,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环绕邺城的周围相继修建了为数众多的伽蓝寺院与石窟寺群。大统师法上讲经说法的修定寺,大论师道凭集结沙门的宝山寺(即今安阳灵泉寺石窟),以及大禅师僧稠交结显贵的灵山寺(即今安阳小南海石窟)与云门寺……都可以算是这一时期竞相建造的著名寺院。
坛庙窟龛的佛陀造像与袅袅香火,开启了北齐王朝崇尚佛教的层层帷幕,然而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佛教艺术最高水平者,则首推南、北响堂山石窟。
提起南、北响堂山石窟,去过那里的人必定会眉飞色舞地叙述一通南、北响堂山石窟地理概念的根本差异,嚼味“响堂”之名的由来与传说,争辩其间的位置、距离,艳羡那里的奇山秀水,赞叹那里雕刻精美的大佛、菩萨以及华丽耀眼的装饰图案……
其实所谓的南、北响堂山石窟,都开凿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所在的鼓山山脉,地理区划均归邯郸市管辖。属南响堂山者在滏阳河左岸西纸坊鼓山西南麓,隔河可望偏居一隅的古彭城镇(原属河北磁县);属北响堂山者则在和村(原属河北武安县)东南鼓山西麓的腰壁之上,东南距南响堂山约17公里。
除了具象地理概念上的南、北响堂山石窟以外,在北响堂山石窟以东薛村附近的山峁上,还有一处今属峰峰矿区寺后坡村地域、被称为小响堂(水浴寺)的地方。由于这里的石窟、寺院、经幢、碑石与北响堂山石窟以及山下的长乐寺遗址在历史上曾经人文衔接、藕断丝连,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都应当属于北响堂山石窟的范畴。据有关资料显示,南北两个响堂寺共有17个窟室,可以目及的大小造像有4400尊,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碑石、经幢以及相关建筑与附属文物,它们共同构成了南、北响堂山石窟寺群的全部内容。
不管是南响堂、北响堂还是小响堂,俱靠一道苍劲雄浑的鼓山山脉把它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5——6世纪交通尚欠发达的黄河北岸,从上都邺城到下都晋阳,鼓山山脉是必须要逾越经过的一道天然屏障。据金代正隆四年(1159)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记,当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常自邺都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仪”,因此便建造了这座千古不朽的南、北响堂山石窟。不管碑文记载是否真实,北齐文宣帝高洋当年曾数次光顾此地,并兀自赞叹、留恋这里的奇山秀水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对照该地所藏金代正隆四年(1159)石刻碑记与北响堂山石窟现存武平三年(572)唐邕写经记以及小响堂山的武平四年(573)造像和石刻法华经等实物资料,可知南北响堂山的始凿年代应在北齐高洋执政之时,由此可知所谓高洋开凿三石室的记载也大致不会有什么偏差。
除了金代正隆四年(1159)石刻碑记等资料的记载外,唐代高僧道宣还在他的《续高僧传》中娓娓记述隋仁寿年间(601—604)杨坚曾下诏命令磁州地方官员在响堂山石窟建立佛塔,发现“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神鬼”。到了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所谓石窟秘藏高欢的记载,更渲染得活灵活现:东魏武定五年(547)八月,“虚藏齐欢武王(高欢)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臣。及齐之忘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根据这些神秘离奇的记载,后来的人便相继派生出一系列的“高见”与论述。或说:“(东)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欢,建避暑宫于山之麓,欢子(高)澄葬父于佛顶焉。北齐文宣帝时……遂开三石窟”;或将曾被文物考古工作者编为第7窟的“大佛洞”,言之凿凿地称做“高欢墓洞”。
依照《北齐书》与《北史》等正史记载,高欢的陵地应在邺城西北漳水之西一带,“陵曰义平”,而高洋则“葬于武宁陵”,虽未准确说明其具体位置,但都未曾说葬于佛顶,葬于“大窟像背”。造成种种误传的原因,可能与北魏以来历代帝王开窟造像,总是想将自己与佛陀连接在一起,以体现帝王的无比尊贵、佛陀的法力无边有关,加之高洋本人确曾频频光顾南北响堂山的峻岭、青峰,并崇尚佛教,开凿“三石室”,因此,将三大石窟与万人之尊的皇帝高洋联系在一起,从而萌生许多美妙神秘的传说故事,也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了。
虽然熟悉历史的人深知古往今来的诸多附会生造故事中必定包涵有不少的隐衷,但乘兴而来的大多数游客们却并不热心理会一本正经的寻章摘句与考证论说。登上苍翠如黛的鼓山山脉,欣赏精美华丽的佛陀造像与装饰图案,帝王的秘藏、盗贼的绝技、佛陀的灵验以及山川风脉的玄妙奇异等种种荒诞神秘的附会、传说,常常会使人们浮想联翩,游兴倍增!
关于南、北响堂山石窟的规模内涵,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多次进行过认真的勘察记录。大致南响堂山现存大小石窟共有7个,北响堂山则保存大小石窟共有8个,而小响堂山仅仅只存一个石窟。除了三处地点大小石窟之外,还有镌刻于北齐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的维摩诘经摩崖石刻以及上文所说的经幢、碑石与各色古建等附属文物。
游览响堂山石窟,热心的导游总是会带你先去看北响堂山的9个石窟。在9个石窟中,编号为第6窟的大佛洞,常常被游客们簇拥得水泄不通。人们如此留恋青睐第6号石窟,是因为它就是传说中的“高欢墓洞”。平顶方形的偌大石窟,面宽12米,进深11米。宽敞的窟室中间,设置有直接窟顶的中心塔柱。在塔柱的左右前后四面,各开凿大龛一个,龛内各雕造一佛二菩萨一铺。佛像的面庞丰颐圆润,与云冈的绮丽华伟、龙门的清癯纤秀迥然不同;造像服饰的衣纹飞动圆润,满目都是流畅劲挺的高凸线条,与“最推工画梵像”、创立“曹衣出水”绝技的曹仲达笔法竟赫然相似、如出一辙。除了主体造像以外,中心柱四角的线刻异兽,柱础上浮雕的博山炉、神王以及对称双狮,也都雕刻得生动传神、入木三分。而在窟龛顶楣上补缀饰雕的佛塔、帷幕以及蔓草图案等更精细华美,似乎比龙门石窟中同样的题材还要高出一筹。
绕过中心塔柱,细心的导游必定还要带领人们按照佛教礼佛的最尊贵程式右旋前进,走到后面的窟壁之前,每每都要闪烁其辞地叙述一番高欢秘藏的故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喧嚣与发自肺腑的疑惑、惊诧,空旷冰冷的古老石窟,总是被人们虔诚神秘的无限遐想浸润得热浪滚滚,生机盎然!
在北响堂山石窟寺群范围之内,除了神秘的大佛洞外,平面略呈长方形的第3号窟亦颇值得关注欣赏。这一石窟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三壁三龛的独特布局以及以三世佛为主的铺像组合程式。据专家考证,三壁三龛的洞窟形式由云冈石窟三世佛的造像组合演变而来,后流行于北齐一代。不过比起云冈石窟而言,第3号石窟的三壁三龛形式显得更加整齐规范,并由此成为北齐以后三壁三龛式石窟的标准范本。
翻阅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石窟艺术史,人们熟谙北齐石窟艺术的地位与分量,然而提及与之相濡以沫的另一种艺术形式一摩崖刻经,知道的人却不多。
北齐的摩崖刻经,素以分布广泛,规模巨大著称,但大多带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如果说北响堂山是一处皇家经营的石窟寺群的话,那么,保存在这里的摩崖刻经则更得风气先,以其雄浑的气魄、精湛的雕技以及典雅华贵的书艺,代表了北齐摩崖刻经的最高水平。
移步观览响堂山摩崖刻经,不能不光顾被称为“刻经洞”的这处石窟,其与北齐时期开凿的释迦洞、大佛洞三大石窟一起,构成整个北响堂山石窟的核心。关于它的雕刻原委,文献记载说是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曾感于“海手经籍,斯文必传”,“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愿将佛经镌刻在名山之上,“一托贞坚,永垂昭晰”①,以图千古流传,永世不灭。
在北齐皇室的鼎力支持下,唐邕凭借自己显赫的政治地位以及优越的经济实力,从后主高纬天统四年(568)三月开始,到武平三年(572)五月结束,雇工数百,历时四年,终于完成了这座满刻有《维摩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四部长篇经书的石窟雕造。
在印刷技术尚不发达的北齐时期,依靠锤钎斧凿等原始工具,在坚硬的石壁上錾崖镌字,将繁冗生涩的经书准确无误地镌刻出来,不知需要花费多少心血,洒下多少汗水!工匠的智慧,宗教的魅力,促成了这座特殊石窟的雕造,凝神注目,那四面石壁上密密麻麻的娟秀文字,似乎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宗教含义,它所昭示给今人的,将是一座用精气魂魄所铸就的不朽丰碑!
游罢神秘庄严的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所带给人们的,则是无尽的洒脱,无尽的秀美!
开凿在这里的7个石窟,分上下两层排布在鼓山南麓陡峭笔直的断崖上,其中上层2窟,下层5窟,其形制为支提与三壁三龛方形平顶洞,计有造像3700多尊。远望好似一位巍然伫立的赳赳武士,令人不禁游兴大增,精神为之一振。就窟室的形状、造像的风格以及题材的内容,与北响堂山石窟相比,没有多少严格的差异。然而被称为“华严洞”、“般若洞”、“阿弥陀洞”的1、2、4三窟内的娟秀刻经,非常醒目,常常会吸引无数的游人去驻足围观。
这是3座满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经书的石窟,字体健劲,丰姿绰约,已经没有了北响堂山唐邕刻经的几分苍凉,几分压抑。那楷隶相间的规范结体、游刃有余的流畅笔势,展示给人们的,已是一个近乎于完美的艺术境界。
根据第2号窟门外所保存的天统元年(565)邺县功曹李洪运雕造石窟碑记记载,我们知道高欢当年往来两都时,曾驻跸这里。当他看到寺庙的建筑简陋破败,雕刻陈设也远远不及其他寺庙,于是便突发慈悲,慨然捐资“斩此石山,兴建图庙”。由此看来,南响堂山石窟也应该属于皇家开凿的石窟,在身份与地位上,亦绝不亚于北响堂山的石窟。
与南、北响堂山石窟相比,小响堂山石窟虽说仅有一个窟室,但雄伟的中心塔柱,惟妙惟肖的雕造技艺以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基本铺像组合程式,也足以使它成为游人瞩目的亮点。据考证,隋唐以后的基本铺像组合程式,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承传关系。诚如此,小响堂山石窟在中国石窟寺艺术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便毋须多加解释了!
按照中国石窟寺建筑的组合规律,寺中、殿前一般都要附建高大雄伟的佛塔,借以渲染佛陀的至高无上、法界的广阔无边。响堂山的石窟原来到底有多少座佛塔,现在已无从得知。惟南响堂山石窟寺外右方至今尚巍然矗立宋建七级八角密檐式砖塔一座,因全系红砖砌造,故称“红塔”。红塔高高耸立在鼓山之上,与石窟、青峰、峻岭、流水相映互衬,别有一番动人的景象。每当深秋将至,树叶泛黄的时节,红塔一侧的诗人、画家与摄影家总是不绝如缕,他们赞赏红塔、黄叶的美丽,常常会在这里驻足观赏,留连忘返,并希冀尽快获得佛陀、红塔所赐予的无限灵感!
除了高大雄伟的鼓山红塔以外,南响堂山寺内茂密神奇的“槐抱柏”,以及曾被周恩来命名的“无名树”,也是游人们必定踊跃一去的胜景。作为南响堂山寺文物保管所的所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响堂山石窟的枢纽。每逢旅游旺季到来的时候,奇异繁茂的“槐抱柏”以及非同凡响的“无名树”总是婆娑摇曳、英姿焕发,热诚地向人们投以亲切的问候,大有黄山迎客松那样的绰约丰姿、那样的雍容气度。
在高齐王朝“君临万邦”的时候,响堂山作为皇家卵翼的一处石窟寺群,生民百姓是绝少可以来这里一览佛容的。等到高齐政权土崩瓦解之后,这里虽说禁令大开,但昔日甚嚣尘上的大规模石窟开凿活动也不得不宣告结束。从隋唐以降直至宋明各代,寺僧、施主以及州郡官员曾不惜仆仆风尘往来山上山下,唇干舌躁地“讲经说法”,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减割家珍”,造像祈福。然而毕竟不再是皇权显赫的年月了,那些勉强雕造起来的小窟弱像,在雄奇壮美的高齐石窟面前,竟然是那么孱弱、猥琐,那么贫瘠、矮小!
不管世事如何翻转变幻,倒是一片痴情的善男信女以及附庸风雅的文人学士却依旧不顾旅途遥远、山路艰难,车马劳顿地往来于南北响堂山之间,投下虔诚的情感,获得巨大的心理享受。遍布各处石窟寺石碑、壁龛间的发愿文、题记以及诗赋文墨,生动鲜活地定格下各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投影、遗痕,多少能给曾是帝王君主的南北响堂山带来一点质朴无华的世俗色彩!
“高齐三万八千寺,血脉一缕在响堂”。在丝绸之路上无数座石窟中流连寻觅,响堂山的名字也许并不如云冈、龙门那样闻名遐迩、深入人心,然而在中国石窟艺术史发展变化的逶迤长廊里,响堂山所起到的独特承传作用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作为绵延近半个世纪的皇家石窟寺群,响堂山是当之无愧的一颗明珠;作为中国石窟艺术继往开来的一个历史性标杆,响堂山将永远是最响、最亮的一个不朽符号!
注释:
①北响堂寺唐邕刻经铭记。
河北北响堂山石窟第3窟唐邕写经造像碑局部
● 唐邕写经造像碑局部。碑文楷书,凿刻在三尊一铺的窟龛造像之下,尽管窟龛一侧已经残缺,但虔诚、繁复的发愿文中,仍可窥视出当年贵戚豪门奢华的佞佛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