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沧桑篇 古道探秘:青泥岭下北城子——青泥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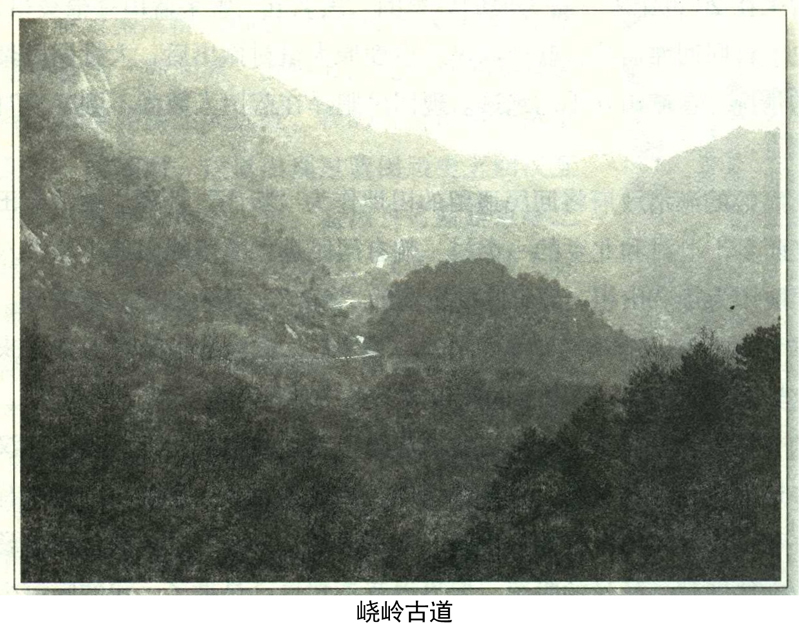
走出“回回滩”,与“回回滩”毗连的沼泽地,正是当年芦苇数里遮天蔽日的芦苇荡。这里曾是灞河湿地水鸟的乐园。每逢盛夏这里鹭飞莺啼,水鸟唧唧,水映苍山,绿波荡漾。春咏烟柳,夏合芙蓉,秋观落日,冬唱大风,真是一块人间乐土也。然而时过境迁,如今芦荡已荡然无存,人与鸟和谐相处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了。此时,落叶正无声地从树上缓缓地飘落下来,在泥土上叠印出大自然的秋韵。果实成熟了,在枝杈间露出了迷人的色泽。但是,那美丽的瞬间却十分暂短,随着叶片的飘落,它完成了一个生物生命的轮回。它们像是天空中那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云锦。大自然周而复始,阐释着人生一首永恒的秋赋,它充满了秋色的悲凉。
离开昔日的芦苇荡向南行数百米,眼前村落雁行排开,过南河后的第一个村落就是大寨村。问及当地村人村名的来历,多少人竟不知所出。后来一位衣冠整洁手扶拐杖的白须老人告诉我们说,“村名来历是由设屯驻军而起”。回来后查阅史志资料得知,这座位于县城南一公里灞河南岸的村寨,因在晋时青泥军前哨设首寨于此,而得名为大寨村。其周围东南连接的还有火烧寨、张军寨、新寨、韩寨、乐寨、冯林寨、蓝门寨等村寨也,如一字长蛇阵沿山排列布局,这些村子都是古代设屯驻军的地方。后来我们又到张军寨,一个老汉告诉我们说,他们村子居住的乡民多为屯军的后代,并有清时的家谱详细地记载了军屯设立及族人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口碑资料与史料相互印证,更证实了大寨等村作为军屯历史的可信性。
设在青泥岭下的这些星罗棋布的村寨,如铁桶般扼住了古蓝关七盘坡与蓝溪峪的出口,形成了一夫把守万夫难开之势。从古蓝关道走出的军队经历了古道险途、长途跋涉,强悍的军队早已成为了强弩之末疲惫之师。一支养精蓄锐的屯兵阻扼于蓝溪峪口青泥岭下,远来的军队如何能够战胜一支以逸待劳的军屯生力军?据历史记载,当年沛公刘邦从彭城誓师进兵武关而略秦,当来到峣关坚城之下,面对坚城利器根本无法攻取,正是张良等人献计,用大量金银收买了屠夫出身的守将,待其放松警惕,方攻破峣关,敲开了大秦帝国的大门。后刘邦又率部绕过篑山登白鹿原并屯兵霸上,使秦王子婴终于不战而降,祖龙基业相传三世而亡。后来的唐与吐蕃蓝田之战,唐大将郭子仪在青泥岭上遍插旌旗,虚张声势,用“疑兵阵”将青泥岭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擅长骑射的彪悍的吐蕃兵,望之心惊胆颤,不知唐军究竟有多少人,稍一接战便望风而逃,这个战役后来成为大唐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令公郭子仪的大名从此也不胫而走,成为大唐一张克敌制胜的王牌。
而距大寨、张军寨、新寨、乐寨等村庄数公里,遥遥相望高高耸立的山峦便是有名的青泥岭所在地。青泥岭又名峣山、峣岭,与县城隔河遥对约10公里。东到悟真峪,西至辋川,长约10公里,通称为青泥岭,主峰高出县城1137米。其东有峣山,中部有七盘山,北有虎头山、清灵山,南有照壁山,西有薛家山。秦楚大道即行经岭上,沿途有七盘坡、乱石岔、鸡头关、风门子、六郎关、大小筝坡关(又称大小坡脑)诸要隘,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古道上令人望而生畏的险要去处。
青泥岭下大寨村南数里,有一村落名营上村,历史上又有北营上和南营上之分。此村处于篑山脚下,辋河东侧,其南营上村地势高峻,整个台塬高出地面十数米,两水相夹,绕村而过,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就是蓝田历史上有名的北城子,即古代青泥关的遗址。据《蓝田县志》记载,青泥关“遗址在今大寨乡(今已为蓝关镇)营上村北的‘北城子’”。据《水经注》记载,北城子系北魏时所建,并设有青泥军在此驻守。后来此处即成为唐时蓝田道(即西安至蓝田到牧护关)与商州接界所置六驿(灞桥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驿、蓝桥驿、蓝溪驿中)离县城最近的驿站青泥驿。据《读史方舆纪要》卷53《蓝田峣柳城》记,“今县治也”,又云“青泥城在县南七里……唐时置青泥驿”。唐代马车日行约七八十里,故青泥驿为出京后第一宿处。
和现在的高速公路建设一样,驿道的管理与建设,也是封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建设项目,驿道的建设与发展状况,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形势。然而,驿站是如何管理通行的,历朝历代管理各不相同。据史书记载:秦代的通行凭证有“符”“符券”“符传”“封传”等。汉代通行印信,自天子以至百姓有玺、节、符、传等。到了唐代,交通往来的凭证称为“驿券”“传符”“过所”等。史载符的制作质料有两种,一种是金属制成(有铜、银等),一种是非金属制成的,有木制、骨制、纸制等,而且符必须要盖相应级别的官印才能生效。宋代的通行印信,主要是驿和的檄牌两类,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以及传信牌等。金字牌(为朱漆金字)日行四百里,为邮递最快者,专供皇帝、敕书及军机要务所用,由枢密院和尚书省所掌管。青字牌(为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为处理朝廷紧急公务所用。红字牌(黑漆红字)与青字牌作用类同,限日行三百里、传信牌乃军队所用,为坚木朱漆所做,正反面皆刻字,字为“某路传信牌”对分两半,用时领兵者持一,官司持一。驿站铺兵异常辛苦,元朝有记载,说那些传递文件的“铺兵”们,“皆腰革带,悬铃,持雨衣;赍文件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符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豹也”。
青泥驿作为离开京都长安后的第一宿处,驿站常常车水马龙,南来北往的、商贾僧侣、文人学士、驿卒贩夫之流,川流不息,络绎不绝,一派繁忙之景象。
青泥驿作为县城附近的官驿,迎来送往的官场活动也十分频繁。这些官场行为,从唐大历十才子之一诗人钱起的诗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年钱起初任蓝田县尉,在青泥驿“迎献”大诗人王维时,曾写《清泥驿迎献王侍御》一首,诗曰:
候馆扫清昼,使车出明光。森森入郭树,一道引飞霜。
仰视骢花白,多惭绶色黄。鹪鹩无羽翼,愿假宪乌翔。
《全唐诗·朱元衡同洛阳诸公钱卢起居》诗云:
暮宿清泥驿,烦群泪满缨。
可见青泥驿作为官驿,接待过往官员是十分繁忙的。同时朝臣赐死亦有在此驿的,如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召宦官山南东道监军陈鸿志还京,遣使杖杀于此驿。可见驿馆也是具有政府行为的官办机构。
离开昔日的芦苇荡向南行数百米,眼前村落雁行排开,过南河后的第一个村落就是大寨村。问及当地村人村名的来历,多少人竟不知所出。后来一位衣冠整洁手扶拐杖的白须老人告诉我们说,“村名来历是由设屯驻军而起”。回来后查阅史志资料得知,这座位于县城南一公里灞河南岸的村寨,因在晋时青泥军前哨设首寨于此,而得名为大寨村。其周围东南连接的还有火烧寨、张军寨、新寨、韩寨、乐寨、冯林寨、蓝门寨等村寨也,如一字长蛇阵沿山排列布局,这些村子都是古代设屯驻军的地方。后来我们又到张军寨,一个老汉告诉我们说,他们村子居住的乡民多为屯军的后代,并有清时的家谱详细地记载了军屯设立及族人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口碑资料与史料相互印证,更证实了大寨等村作为军屯历史的可信性。
设在青泥岭下的这些星罗棋布的村寨,如铁桶般扼住了古蓝关七盘坡与蓝溪峪的出口,形成了一夫把守万夫难开之势。从古蓝关道走出的军队经历了古道险途、长途跋涉,强悍的军队早已成为了强弩之末疲惫之师。一支养精蓄锐的屯兵阻扼于蓝溪峪口青泥岭下,远来的军队如何能够战胜一支以逸待劳的军屯生力军?据历史记载,当年沛公刘邦从彭城誓师进兵武关而略秦,当来到峣关坚城之下,面对坚城利器根本无法攻取,正是张良等人献计,用大量金银收买了屠夫出身的守将,待其放松警惕,方攻破峣关,敲开了大秦帝国的大门。后刘邦又率部绕过篑山登白鹿原并屯兵霸上,使秦王子婴终于不战而降,祖龙基业相传三世而亡。后来的唐与吐蕃蓝田之战,唐大将郭子仪在青泥岭上遍插旌旗,虚张声势,用“疑兵阵”将青泥岭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擅长骑射的彪悍的吐蕃兵,望之心惊胆颤,不知唐军究竟有多少人,稍一接战便望风而逃,这个战役后来成为大唐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令公郭子仪的大名从此也不胫而走,成为大唐一张克敌制胜的王牌。
而距大寨、张军寨、新寨、乐寨等村庄数公里,遥遥相望高高耸立的山峦便是有名的青泥岭所在地。青泥岭又名峣山、峣岭,与县城隔河遥对约10公里。东到悟真峪,西至辋川,长约10公里,通称为青泥岭,主峰高出县城1137米。其东有峣山,中部有七盘山,北有虎头山、清灵山,南有照壁山,西有薛家山。秦楚大道即行经岭上,沿途有七盘坡、乱石岔、鸡头关、风门子、六郎关、大小筝坡关(又称大小坡脑)诸要隘,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古道上令人望而生畏的险要去处。
青泥岭下大寨村南数里,有一村落名营上村,历史上又有北营上和南营上之分。此村处于篑山脚下,辋河东侧,其南营上村地势高峻,整个台塬高出地面十数米,两水相夹,绕村而过,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就是蓝田历史上有名的北城子,即古代青泥关的遗址。据《蓝田县志》记载,青泥关“遗址在今大寨乡(今已为蓝关镇)营上村北的‘北城子’”。据《水经注》记载,北城子系北魏时所建,并设有青泥军在此驻守。后来此处即成为唐时蓝田道(即西安至蓝田到牧护关)与商州接界所置六驿(灞桥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驿、蓝桥驿、蓝溪驿中)离县城最近的驿站青泥驿。据《读史方舆纪要》卷53《蓝田峣柳城》记,“今县治也”,又云“青泥城在县南七里……唐时置青泥驿”。唐代马车日行约七八十里,故青泥驿为出京后第一宿处。
和现在的高速公路建设一样,驿道的管理与建设,也是封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建设项目,驿道的建设与发展状况,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形势。然而,驿站是如何管理通行的,历朝历代管理各不相同。据史书记载:秦代的通行凭证有“符”“符券”“符传”“封传”等。汉代通行印信,自天子以至百姓有玺、节、符、传等。到了唐代,交通往来的凭证称为“驿券”“传符”“过所”等。史载符的制作质料有两种,一种是金属制成(有铜、银等),一种是非金属制成的,有木制、骨制、纸制等,而且符必须要盖相应级别的官印才能生效。宋代的通行印信,主要是驿和的檄牌两类,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以及传信牌等。金字牌(为朱漆金字)日行四百里,为邮递最快者,专供皇帝、敕书及军机要务所用,由枢密院和尚书省所掌管。青字牌(为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为处理朝廷紧急公务所用。红字牌(黑漆红字)与青字牌作用类同,限日行三百里、传信牌乃军队所用,为坚木朱漆所做,正反面皆刻字,字为“某路传信牌”对分两半,用时领兵者持一,官司持一。驿站铺兵异常辛苦,元朝有记载,说那些传递文件的“铺兵”们,“皆腰革带,悬铃,持雨衣;赍文件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符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豹也”。
青泥驿作为离开京都长安后的第一宿处,驿站常常车水马龙,南来北往的、商贾僧侣、文人学士、驿卒贩夫之流,川流不息,络绎不绝,一派繁忙之景象。
青泥驿作为县城附近的官驿,迎来送往的官场活动也十分频繁。这些官场行为,从唐大历十才子之一诗人钱起的诗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年钱起初任蓝田县尉,在青泥驿“迎献”大诗人王维时,曾写《清泥驿迎献王侍御》一首,诗曰:
候馆扫清昼,使车出明光。森森入郭树,一道引飞霜。
仰视骢花白,多惭绶色黄。鹪鹩无羽翼,愿假宪乌翔。
《全唐诗·朱元衡同洛阳诸公钱卢起居》诗云:
暮宿清泥驿,烦群泪满缨。
可见青泥驿作为官驿,接待过往官员是十分繁忙的。同时朝臣赐死亦有在此驿的,如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召宦官山南东道监军陈鸿志还京,遣使杖杀于此驿。可见驿馆也是具有政府行为的官办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