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孜尔遗址和墓葬看龟兹青铜时代文化
作者:张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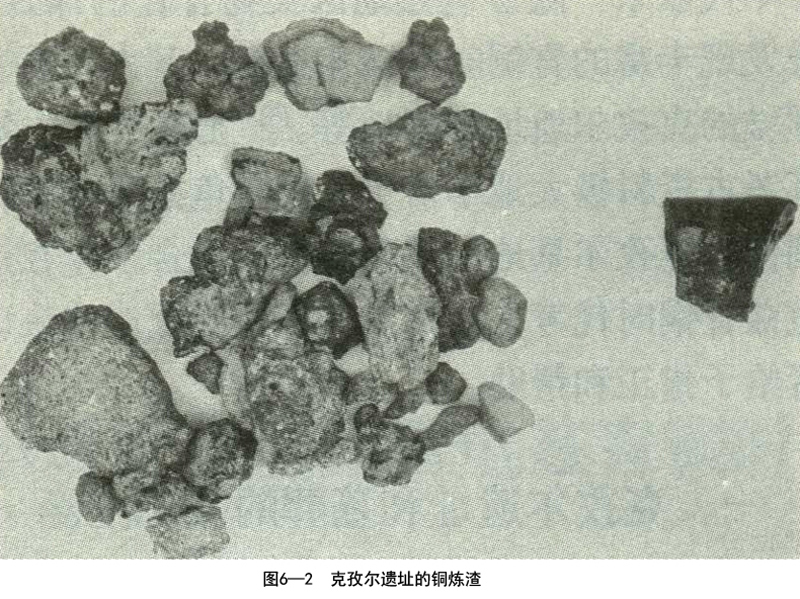










近十年,新疆青铜时代考古不断发现更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其文化内涵既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又反映出各周边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展示出新疆青铜时代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内涵,以及各区系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亦取得一定的成绩。如王炳华先生的《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①,陈戈先生的《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②、《新疆史前文化》③、《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④,水涛先生的《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⑤,安志敏先生的《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⑥等文,对新疆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分类和界定、文化内涵和相互联系等有关问题作了阐述,其丰富和翔实的考古资料和学术观点,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识。
龟兹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⑦50年代曾调查并发掘过阿克苏东遗址⑧、喀拉玉尔衮遗址⑨和库车的哈拉墩遗址。⑩80年代以来,随着龟兹地区文物普查的深入,在库车河、渭干河流域曾发现丰富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其中主要有库车的麻扎甫塘墓地、拜城的克孜尔遗址和墓地等。(11)尤其是克孜尔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其考古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龟兹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的认识。本文则借助克孜尔墓地的整理资料,结合多年在这一地区调查的感知,就龟兹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及其有关问题谈些认识,希望对此感兴趣的学者给予指正和帮助。
一、克孜尔遗址和墓葬的文化内涵
克孜尔遗址和墓地位于拜城盆地东南隅的克孜尔乡境。源于天山冰川的克孜尔河及木扎特河在此融汇东流,经克孜尔千佛洞穿越确勒塔格山谷后流入库车、新和、沙雅三县绿洲。遗址和墓地择于克孜尔河的东西岸台地,于1989年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中发现。(12)为配合克孜尔水库建设工程,1990—1992年的三年中做了四次抢救性的发掘。发掘墓葬160座,出土陶、石、骨、铜器等文化遗物和体质人类学资料。遗址居于墓地的西部,地表观察到居住遗址和炼铜遗迹。(图6—1,克孜尔遗址的石锤)
遗址散露着破碎的陶器、石磨盘、石斧、石锤、残坩埚、炼渣、炭灰堆积,以及丰厚的矿料堆积等与冶铜活动有关的文化遗物。从对遗址内的陶器质地和器型观察,其文化内涵的性质同墓葬相一致。(图6—2,克孜尔遗址的铜炼渣)
墓葬皆集中分布于遗址的东端而临河床,葬区与居住区之间有明显的分界。每座墓之间没有打破或叠压现象,说明这是各有其独自封土规则的定穴安葬的公共墓地。考古资料仍在整理之中,现将墓葬的文化内涵概况介绍如次,以助研究分析。
墓葬地表皆有沙质黄土堆成的封土为标志,封堆呈圆锥状,低径5米~20米,残高0.6米~1.5米。封堆底下即为圆角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室,墓室长1.5米~2米、宽0.8米~1.5米、深0.8米~2米,无葬具。埋葬习俗为一次葬和二次葬。依墓主人的骨殖处理方式,则分为单人一次葬和二次葬,多人的一次葬和二次葬。埋葬姿势主要有侧身屈肢,其中以头西面北或头西面南的侧身屈肢葬为典型。随葬遗物中有组合的陶器,大都置于墓主人的头部的西壁。男性往往随葬有小铜刀、锥或砺石;女性则随葬有纺轮、珠饰、耳环、颈饰等。墓葬中随葬品贫乏,有的墓内仅出土一块彩陶片或一小块孔雀石,个别墓葬则无任何随葬品。墓地出土的文物中以陶器最多,其中彩陶器占有一定的数量。其一,陶器皆手制的夹砂红陶或红褐陶。陶质不细密,火候较低,陶器内外往往要施一层土黄色陶衣。器物造型简单,皆以鼓腹、球腹的圆底器为特征。主要的器物组合为敞口釜、带流釜、盆、钵、勺、碗等。器物分类简单,个体变异较差,显示出原始、粗犷的特点。其二,随葬的陶器都是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日用器皿,无论是素陶还是彩陶的炊煮器如敞口釜、带流釜,或是盛储器类的盆、钵等器底,均有炊烧的烟炱。同时,在圆底部均附着一层含粗颗粒的石英砂,个别盆、钵的底部亦是如此。其三,对陶器的腹壁、器底观察,系采用泥片粘贴制陶法,具有自身制陶特点,彩陶纹饰凝重而单一,通体彩绘亦是特点。彩色为红色或紫红色,纹饰主要为宽条的带状纹,多组分层重叠的正三角纹、水波纹(折线纹)、网格纹等,显示出彩陶淳厚质朴的艺术形式。其装饰手法采用疏与密、斜与正的相互陪衬,暗中透亮的表现层次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图6—3,克孜尔墓葬出土的彩陶)
二、克孜尔铜器种类特征及相关问题
克孜尔墓葬出土铜器数量不多,目前整理中的130座墓葬共出土大小铜器40件,不足出土文物总量的1/10。其种类主要有刀、锥、颈饰、耳环、纺轮、扣饰等简单的生活和装饰等小件用品。(图6—4,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镜)
其中出土完整和残缺的小铜刀9件,依据柄首的形状可分两种类型:A型为直柄式小刀,扁平长条状,弧背弧刃,柄部和刃部稍有分界或分界不明显,一般长13.4厘米~15.8厘米、宽1.4厘米~1.6厘米、厚约0.2厘米;B型为环首直柄式小刀,扁平长条状,柄端呈环状,柄刃部有明显分界,通长14厘米~19.5厘米、宽1.7厘米~2厘米、厚0.2厘米。铜刀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刃部经热加工。出土铜斧一件,扁平长条状,弧刃,有銎,长17.8厘米、宽4.7厘米。铜镜二件,均为圆形,拱钮。镜背有狭直或斜缘,直径12.8厘米~13.4厘米。铜斧和铜镜为合范工艺铸造,铜斧亦为内、外范的合铸。(图6—5,克孜尔墓葬出土的动物纹铜扣)
而其他的如锥、耳环等则为锻打和卷曲而成。出土的铜器,曾初选三件标本请新疆有色地质勘探局703大队测试中心做了测定。其中90BKKM27出土的铜渣块,经测定为赤铜,铜含量为70%,孔雀石含量为20%;同墓出土的一件铜饰残件测量为红铜,铜含量达92%。91BKKM6出土的铜矿石,经测定为赤铜矿,铜含量达8%。(图6—6,克孜尔墓葬出土的勺形铜器)
综上所述,克孜尔出土的铜器数量少,器型简单,铸制粗放,多为日用的小工具和饰物,较大型的铜器如马具、兵器等没有发现。铜器测定表明为红铜制品,这说明铜器的使用还只是处在很小的范围内,铜器的作用还十分微小。(图6—7,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纺轮)
在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用具中石器仍是普遍的,尤其是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磨制石刀和石镰工具表明,原始的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同时,墓葬中普遍有羊等牲畜随葬,则又表明家庭的畜牧饲养亦是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家庭饮食生活所使用的陶器由简单的器物组合而成,主要是圆底鼓腹的敞口釜、带流釜、圆底盆(钵)、单耳碗(勺杯)等。彩绘纹饰的母题主要有正三角纹、水波纹(折线纹)、条带纹、网格纹等,构成了克孜尔墓地文化内涵的主要特征。(图6—8,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项圈)
三、克孜尔时代和邻近文化遗存的关系
关于克孜尔墓地的绝对年代,我们曾采集了一些墓葬中的朽木标本做了年代测定,初步测出五个数据,其时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13)根据墓葬中的彩陶、铜器和磨制的石镰,结合近些年来邻近的察吾乎沟墓地、群巴克墓地的考古发掘,其文化性质和内涵与克孜尔墓地相比较,可作龟兹青铜文化年代的参证。
察吾乎沟口基地位于天山南麓的和静县哈拉毛墩乡。1983—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曾对一、二、三号墓地进行了部分发掘。(14)其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亦对一、二、三、四、五号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15)两个考古单位共发掘墓葬四百余座,取得了丰硕的考古资料。
墓葬主要特征是在地表上都有石围或石堆标志,墓室卵石砌成长条形、长圆形或圆形。有的在墓口上棚盖大石板或木头,有的在一侧有短墓道。基本上都是多人二次合葬,个别的系一次葬。葬式为仰身或侧身屈肢,头向西或西北。在主墓室周围往往有马头或牛头坑和儿童墓。儿童墓既有单人一次葬,亦有多人二次合葬。随葬品主要有陶、铜、木、石、骨、铁器等,其中以陶器最多。陶器主要为带流罐、单耳罐、双耳罐、釜、单耳小杯(勺杯)、壶、钵等,其中带流罐最多,且为特征典型的陶器。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一般先上一层红色陶衣,再在绘彩处敷一层黄白色陶衣,其上绘红色纹饰,少数是在红色陶衣上直接绘黑彩。纹饰多绘于器物的上部或颈肩处,少数通体绘彩。最有特征的是在器物的颈部绘一周内填各种花纹的斜条带,这种斜条带纹,如果用右手把持器物时,正好面对他人,很有夸示审美效用。彩绘花纹主要有三角纹、网格纹、棋格纹、折线纹、回纹、菱格纹、斜条纹等。
出土铜器比较丰富,其中一号墓地中的138座墓出土铜器170件,数量仅次于陶器。主要有刀、锥、马衔、镞、镜、带钩、针、马镳、碗、匕等各种形状的铜饰。(16)五号墓中的24座墓出土铜器12件,主要有刀、锥、马衔、铜扣、珠饰等。(17)
察吾乎沟口墓地的绝对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和新疆地震局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三十多个数据,其绝对年代大约距今2500年~3000年,亦公元前1000—前500年。(18)同时,在简报中亦作了分期的探讨,认为五号墓地为察吾乎沟文化的早期阶段,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五号墓地的文化特征是埋葬制度流行单人一次葬,随葬品都比较贫乏。一般有一、二件,铜器少,不见铁器。随葬陶器的组合是釜、带流罐、带流杯、勺杯等,陶质较粗糙,火候较低,器表不平整。
群巴克墓地位于轮台县群巴克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先后三次发掘墓葬43座。(19)墓葬地表有圜丘形封堆,封土下有一至数个竖穴土坑墓室,多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有的墓室一侧有短浅墓道,墓室中心和四周立木桩,口部棚盖木。个别墓葬没有地面之下的墓室,而是在地面之上直接用木桩栽立成墓室。有的墓葬保存焚烧遗迹。大部分墓实行多人二次合葬,一墓多达数十人,骨殖散乱。少数墓为一人一次葬或二人一次葬,一般仰身或侧身屈肢,头向西北,在主墓室周围的边缘往往有儿童墓和马头等牲畜坑。儿童墓单人或多人一次葬、二次葬都有。
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木器等。陶器有带流罐、单耳罐、双耳罐、单耳杯、壶、钵等。同样以带流罐为特征。彩陶器是先敷一层红色陶衣,再涂上一层陶衣,而后绘红色或黑色纹饰。花纹一般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母题主要是内填平行斜线的正倒三角纹、网格纹、竖条纹等。除铜器外,铁器较多,主要有铁刀、铁镰、铁剑、铁锥等。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与察吾乎沟口墓葬基本一致,距今2500年~3000年,亦即公元前1000—前500年左右。(20)
上述三处墓地比较,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的数据相接近,总体文化内涵亦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如单人或双人的侧身屈肢葬式,头置西或西北,多人的二次合葬,以及普遍的带流陶器、环首或直柄的小铜刀、扣饰等。同时,它们之间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地表的封堆、墓室的结构以及葬具等。尤其是带流的陶器,在察吾乎沟口墓地出土的带流罐,体型较小,制作较精,瘦高,胚薄,流口较平,皆为平底,装饰纹样具有审美效用,为盛储器类;在群巴克墓地出土的带流罐,则体型稍大,平底和圆底皆有,流口上翘,球形腹为特点,彩绘装饰性较差;而在克孜尔出土的带流器,造型普遍大,皆以圆形底、鼓腹或球腹的炊煮器为特征,其彩纹亦有区别。如是则三处墓地之间的差别,应是同一种文化中不同类型的客观反映。换言之,即是不同地域或不同类型之间差别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克孜尔墓地的发掘,可以说是新疆第一次在天山南麓的西部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其墓地的性质和文化内涵特征比较明显,地理位置又同西部天山地带的中亚地区接壤。从已知的中亚青铜文化资料相比较,克孜尔的墓葬形制、墓葬习俗、陶器和彩陶式样、磨制的石镰形制等,在一定程度上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费尔干纳青铜时代的楚斯特文化(21),以及南土库曼斯坦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内涵,亦有着相关联系。(22)这类来自中亚或西亚文化相关的信息,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其复杂性和曲折性的文化关系,亦是龟兹文化发展的线索,值得深入认识。
综上所述,克孜尔墓地同周邻地区青铜文化相比,其文化性质属于青铜时代的范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其文化内涵表明同周邻青铜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交流,同时又显示出自身的特点。龟兹青铜时代考古多元文化的成分来源是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四、龟兹古铜矿冶遗迹的初步调查
据汉文史籍所载,至迟到公元前二世纪时,龟兹的冶铸在西域36国之中已享有盛誉。(23)就自然条件而言,龟兹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主要铜矿分布在库车、拜城两地。(24)近些年,笔者曾同库车县文管所、拜城县文管所、北京科技大学从事冶金史研究的老师、同事们调查过一些早期采矿和冶铜活动的遗迹,现将调查概况综述如下。
(一)库车河流域的冶铜遗迹
库车河源于天山南麓的哈里克乌山东段,因其源头流经地域和消失位置均在库车境内而得名。其县城北部天山坳陷中的上第三系沉积层里含有丰富的铜矿、煤、铁等矿藏资源。其中铜矿开采冶炼的时代早,规模大,故库车河亦有“铜厂河”俗称。曾调查过的古铜矿遗迹主要有:
1.库兰康铜矿
位于库车县城北约22公里苏巴什村内的“独—库”公路西约7公里处。矿体产于第三系中新统苍棕色岩组内。矿床的矿化带长约15公里,主要集中分布于库兰康、巴拉艾肯、喀让依西克三个地段的铜矿点。当地俗称“铜厂”和“康村”冶铜遗址。其中库兰康铜矿体长约4公里,矿层厚度2米~8.5米;巴拉艾肯矿段长约3公里多;喀让依西克矿段的矿体规模较小、分散。古采坑附近发现有采矿工具的石斧、石锤、石球,以及炼渣、破碎矿石和木炭堆积。
2.恰克玛克铜矿
位于库车县城北约45公里库车河畔的恰克玛克一带。铜矿带东西绵延长约10公里,分属恰克玛克、苏康、巴什克其克、克孜力亚和窝特拉克五个地段的矿点。
恰克玛克铜矿带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其中河东矿体有两个含绿色矿层,均呈带状分布。第一层矿体长约1公里,矿带厚约1米~2米;第二层矿带长约500米,矿带厚约0.5米,铜矿物为孔雀石氯铜矿。
苏康含铜砂岩矿点位于巴什克其克沟南,含铜砂矿体长约500多米,厚达3米,铜矿物主要是赤铜矿、黑铜矿。
巴什克其克含铜砂岩矿体,分布于巴什克其克沟内,为灰色砂砾岩,矿化较好的矿体长约50米,厚达3米。
克孜力亚含铜矿体为灰褐色石英砂岩,矿体长约300米,厚达0.7米。矿化物主要是赤铜矿、黑铜矿、孔雀石。
3.依里木扎尔得铜矿
分布于库车县城北150公里。库车河的依里木扎尔得沟西。矿体以黄铜为主,呈透镜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调查到的铜矿遗迹中恰克玛克所属铜矿点含铜丰富,铜品位高达2%~3%。同时附近有大量的炼铜遗存和采矿遗迹。曾调查到破碎的矿石原料、堆积的炼渣,以及采矿使用的石质工具等。其中采矿坑有多处,如巴什克其克铜矿,东侧的古矿洞(坑)分布四层,每层坑进深达几十米,坑洞口低矮,高约70厘米;西侧的古矿坑也有几条采矿点。调查表明,所开采的矿石运到附近的河畔进行初炼。我们在冶铜遗址中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锤之类的工具,人工破碎的矿料、熔炼的炉渣、炼渣等文化遗物。
1986年9月,笔者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原北京钢铁学院)吴坤仪教授一行在此调查到一处汉代炼铜遗址,采集到有关冶炼标本的测试分析表明,此处冶炼方法是使用了硫化矿冶铜技术,这类冶铜遗址同邻近的天山北部奴拉赛铜矿、冶炼遗址相同。尼勒克县的奴拉赛冶铜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2650±170年和2440±75年,即公元前600年左右。(25)如是,则库车恰克玛克炼铜遗址使用的“硫化铜—冰铜—铜”工艺技术(26),同天山北麓的圆头山和奴拉赛山采矿、冶铜遗址,在冶铜技术方面有着一定的联系,其历史渊源流长。
(二)确勒塔格山麓
确勒塔格山是属天山山脉南部中段的一座前沿山,俗称“前山”。西起温宿县东北,经拜城、新和,终止于库车东境,绵延曲折长约三百余公里,是龟兹文化艺术的宝库,著名的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寺都留下了龟兹历史的辉煌。同时也是“能源”基地,蕴藏着铜、铁、煤、石油、盐、石膏等矿。其中拜城境内的150公里的山麓铜矿甚丰,故有“铜山”之誉。曾发现老虎台的卡捷克托尔、包孜东乡的阿库朗、察尔齐乡的滴水和温巴什乡的土孜勒克艾肯等铜矿,主要调查的铜矿有:
1.滴水铜矿
位于拜城县察尔齐乡西南20公里的木扎特河南岸。滴水铜矿体,即是“铜山”古铜矿遗迹。有三个含矿绿色层,均呈带状自西向东分布。矿石主要为氧化矿石,其中以孔雀石为主,兰铜矿次之,以及少量的铜兰及辉铜矿。穷矿到库姆矿段,矿体长约2.5公里,平均矿层厚0.8米,阿尔特巴勒矿段,矿体长约1.5公里,平均厚0.9米。调查中发现穷矿附近有已开采的老铜矿坑,亦是很早就使用土法开采炼铜的一个老矿区。同时我们在木扎特河畔、滴水石窟寺附近曾发现炼铜遗迹多处。(图6—9,拜城“铜山”炼铜遗址)
2.温巴什铜矿
位于拜城县温巴什乡境内的确勒塔格山麓。主要有土孜勒克艾肯、克尔拉克、喀拉克尔、克尔克什拉克等五个铜矿段,以及吉格代力克村西南的土孜勒克炼铜遗迹、冬买里村的协依和买里斯炼铜遗存,曾采集到矿石、矿渣、陶器残片、坩埚残片等文化遗物。(27)(图6—10,拜城麻扎里亚炼铜遗址)
以上铜矿和冶炼遗存的初步调查资料表明,龟兹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尤其是氧化矿带附着于地表,这对早期懂得很少采矿知识的龟兹人来说,是极易被发现和利用的,这为龟兹青铜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先决条件。只有铜矿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才能发现铜,认识铜,进而冶炼铜。龟兹早期采矿和冶炼的调查与研究,需要考古工作者同有关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合作。
结语
龟兹青铜时代文化的产生有着自身的发展优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易被发现和利用,为早期铜矿开采的冶炼活动提供了物资条件。
第二,库车河、克孜尔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内涵,从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应是定居的绿洲农业文化为主体。定居、农业和制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早期铜矿的开采和冶炼。
第三,考古调查到的古铜矿遗存附近往往都有冶炼遗迹、居住遗址和墓葬。这种三者并存的联系表明了龟兹早期铜器为本地所生产。
第四,龟兹青铜文化内涵同周邻地区青铜文化相比较,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交流。但是其主体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应是龟兹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只是从考古文化的视觉得到的初步认识,是肤浅的、不全面的。龟兹早期冶铸活动有什么发展特点,它同邻近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及其所走的轨迹等等,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多方面的学者给予关注和讨论。
(原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
① 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4)。
② 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载《考古》,1987(4)。
③ 陈戈:《新疆史前文化》,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2)。
④ 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载《考古》,1990(2)。
⑤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见《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 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载《考古》,1996(12)。
⑦ 参见德日进、杨钟健:《中国西部及蒙古新疆几个新石器(或旧石器)之发见》,见《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2卷,1932。
⑧ 参见王永焱:《西北史前文化遗址概况》,载《文物参考资料》,2卷10期。
⑨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研所考古组:《阿克苏县喀拉玉尔衮等古代遗址》,载《学术简述》第1期,1965年11月;新疆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3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⑩ 参见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11)(12) 参见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载《新疆文物》,1995(4)。
(13) 参见张平、陈戈:《新疆发现的石刀、石镰和铜镰》,载《考古与文物》,1991(1)。
(14) 参见《碳十四年代测定一览表》,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集附录一,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艺术出版社,1987。
(1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2);《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90(6)。
(16)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一、二、三、四、五号墓地发掘简报》,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221~275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集),174~260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艺术出版社,1997。
(17)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2(4)。
(18)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沟五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2(2)。
(19)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十二),载《考古》,1985(7);《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十三),载《考古》,1986(7);《14C测定年代数据一览》,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附录,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艺术出版社,1997。
(20)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87(11);《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次、第三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8)。
(2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87(11);《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次、第三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8)。
(22) 参见[苏]孔德涅昔洛夫斯基:《费尔干纳古代农业》,见《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18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南乌兹别克文物》,乌兹别克共和国文化部、ハムザ记念艺术学研究所,创价大学出版会,1991;卢立·A·札德纳普罗、伍斯基撰:《费尔干纳的彩陶文化》,刘文锁译,载《新疆文物》,1998(1)。
(23) 参见杨建华:《萨玛拉文化》,见《考古学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4) 参见《汉书·西域传·龟兹国》,39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梁志祥:《库车县古遗址简介》,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1);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载《新疆文物》, 1995(4);《阿克苏地区普查报告》,载《新疆文物》,1995(4)。以下引用《汉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25) 参见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五),载《文物》,1984(4);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三),载《文物》,1979(12)。
(26) 参见韩汝玢:《近年来冶金考古的一些进展》,见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论文集》二,1994。
(27) 参见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载《新疆文物》,1995(4)。
龟兹文明: 龟兹史地考古研究/张平著.-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